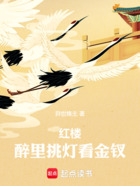
第5章 一篇策论而已,你们的腿在抖什么?
国子监沉重如铁的晨钟撞开层层叠叠的暮春薄雾,三声悠远却自带威仪的嗡鸣,沉沉压在整个官学的脊梁上。
贾琰肃立于肃穆高耸的明伦堂外,一身素白直裰,麻料纹理粗粝,在一众或新或旧、但皆象征前程似锦的监生青衫中,如同茫茫雪地里一截淬炼过的寒梅枯枝,扎眼又带着无声的悲悼。
“看!那就是‘荫监生’?”
细细碎碎的议论声如同阴冷的穿堂风,在肃立的人群缝隙间流淌。
“听说是金陵贾家的旁支?”
“死了爹才换来的名额,啧啧……”
“小声!听说他爹就是在淮扬盐场上,查着查着……人就‘暴毙’了!水深的紧……”
那些字眼像淬了毒的针,细密地扎在耳膜上。
贾琰面上纹丝不动,下颌的线条却绷紧了一分。
他的目光穿透眼前攒动的人头,牢牢钉在大堂门楣上那方太祖手书的泥金大匾——
“明德亲民”。
四个擘窠大字,金漆早已剥落,露出底下深色的木质底胎,斑驳沧桑,却依旧带着开国帝王的铁血遗风,沉甸甸地悬在头顶,压迫得所有进出此门之人难以喘息。
这就是帝国的权力基石,冰冷,坚硬。
“肃——静——!”
监丞一声断喝,如同皮鞭抽破空气。
所有窃窃私语瞬间死寂。
穿着各色襕衫的监生们如同溪流入海般,垂首敛目,鱼贯而入。
脚步声在空旷古老的殿宇里回响,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局促。
贾琰的座位被安排在明伦堂西窗最角落。
窗棂是繁复的冰裂纹格,几经修补,新补的桐油木料混在旧色里。
春日稀薄的阳光费力地穿过这些网格,在他面前粗糙的考卷宣纸上,投下细碎而摇晃的光斑碎片,如同一地难以拾掇的心事。
墨已研浓,狼毫锋锐。
他深吸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久存典籍纸张的霉味、新墨的松烟气息,他缓缓展开面前的考题卷封。
雪白宣纸上一行墨字:
《论君子务本》。
——一个再寻常不过、几乎被历届学子嚼烂了的经义题。
贾琰悬腕、提笔,呼吸沉入丹田。
笔尖饱蘸浓墨,轻轻落在纸上,墨色缓缓晕开,像一滴化不开的浓愁。
父亲严厉的教导在脑海中响起:“考场如战场!文章不必锋芒毕露,招致物议!但求……滴水不漏!”
他凝神聚气,字字落笔千钧:
“君子务本。此‘本’者,根也,源也。非独言孝悌于家门之内,更当正心明辨于庙堂之上、是非黑白之间!
盐政之弊,其表象在于课税之巨额亏空,如体肤疮痈,触目惊心;
然其症结之根本,深埋于权柄倾轧、纲纪驰堕之内腑!
昔管子尝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盐政何如?
江淮盐丁灶户,抛家弃井,形若野鹤散沙;
漕运舟楫名册,虚增浮冒,蛀虫盘踞其中!
此乃仓廪未实,黎庶根基动摇!
而京师权贵,朱门宴饮未歇,膏腴先自满溢!
——此非‘本’失,而大厦将倾之兆也?
溯及盐铁之议,桑弘羊主断专营以夺利,贤良文学倡放任以养民。
然二者皆陷偏隅,未能洞察根本至理:盐之利,如江河之水,当归流以沃原养民,岂容筑堰闸坝以独肥官蠹?
治河之术,疏浚为本,方得源流澄澈;
筑堤为末,徒堵一时溃决。
今盐政只究堤坝(税吏贪墨)之崩颓,不查河道(根本制度与民生)之淤塞朽坏,岂非舍本逐末?
纵累月经年,终为徒劳无功!”
笔锋划过宣纸,发出沉稳单调的“沙沙”声。
字字如刀刻斧凿,力透纸背。没有一丝火气,却字字皆是寸寸斩向顽石的寒铁!
考场落针可闻,唯有墨干笔走之声。
距离稍远,一个江西口音的举子程景明,捏了捏藏在中衣里的银票——那是父亲偷偷塞给他打点关系的,并再三嘱托:“金陵贾家虽大厦将倾,毕竟是百年勋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见着了那位荫监的,莫要轻易得罪……”
他眼角余光飞快地扫向那个素白的身影,正欲估量这“骆驼”的斤两,目光却精准地捕捉到了贾琰因频繁翻阅父亲旧书而在袖口处磨出的毛边!
一丝混杂着怜悯与居高临下的无声嗤笑,悄然爬上了他的嘴角。
紧挨着贾琰的山东监生刘承业,原本只是习惯性斜眼,欲窥探邻座答案片段。
当视线猛然撞见考卷上“盐政”、“权柄倾轧”这几个力透千钧的字眼时,他心头骤然一悸!
他慌忙收回视线,一颗心几乎要跳破胸膛——他的嫡亲伯父,正是掌大周北方盐脉的长芦盐运司运使!
而在考棚最昏暗逼仄的角落,一个衣衫浆洗得发白、面有菜色的寒门监生吴铭,颤抖着地手指死死握着一杆秃笔。
他粗糙、布满裂口与旧伤的十指指甲缝里,深深嵌着永远洗不净的灶盐颗粒的灰白结晶。
当“盐场灶户逃亡者……”
这一行墨字刺入眼帘,瞬间勾起深埋的、亲人在盐课酷吏鞭下挣扎、最终填了沟壑的记忆!
他浑身抑制不住地剧烈颤抖起来,滚烫的泪水模糊了视线,狠狠砸在考卷上,将刚写下的“君子”二字,晕染成一团模糊不堪的墨疙瘩“君孑”
——独子遗民,只剩孤魂!
贾琰笔锋稳健,直入第三页。
正写到“终为徒劳无功”时,一片黑影陡然覆压下来,将他考卷上的光斑彻底吞噬。
贾琰霍然抬头。
一位身着正五品青色鹭鸶补服、面容清癯肃然的官员,已无声无息地立在考案前尺许之处。
那人腰间悬着一块代表身份的素面象牙腰牌,上书镌刻着三个端谨小字:“国子监司业陈景明”。
陈景明一双古井无波的眼眸缓缓扫过他的答卷,从题头“君子务本”,掠过“盐政之弊”,最终停在刚刚落笔的“夫盐铁之议……舍本逐末”的论述之上。
他的目光在此驻留了一息,并未言声。
然而,他竟缓缓伸出枯瘦修长却蕴含力道的手指,越过冰冷的考案边缘,用指尖在那考卷墨迹未干的“本”字左上一点!
那一点,极轻、极快,又似带着某种无声的警示或共鸣!
贾琰握笔的手指猝然绷紧!
一股微不可查的气流从笔端泄出。
那“本”字墨迹未干,被这一拂一压,墨色瞬间微微晕开一点浅淡的湿痕,边缘模糊,犹如一点凝结在史册纸页上、苦涩的泪印。
陈景明自始至终未发一言,甚至连眼波都未曾与贾琰对视一次。
他一拂袍袖,仿佛只是例行巡视,负手于后,便如同来时般无声无息地转身离开了这片考区。
贾琰的目光再次垂落在那行被阳光映照得格外刺眼醒目的字句上:“盐政之弊,在失其本!”
每一个字的笔锋,都尖锐如一把未出鞘的匕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