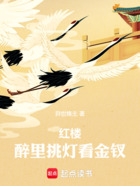
第4章 凤姐堵门,手帕为刀,可惜……我的剑更快
晨光熹微,薄雾如轻纱般笼罩着宁荣后街竹林边的演武场空地。
林间静谧,唯有清寒露水滴落草叶的细微声响。
贾琰的身影在林间空地中腾挪闪转,迅捷如鬼魅。
他手中那柄青锋长剑并非华美装饰之物,每一次挥刺劈撩,都裹挟着锐利的破空嘶鸣,撕裂淡青色的晨雾。
剑光霍霍,如寒潭映月,搅动着周遭沉静的天地之气。
一套剑法渐至尾声,身形回旋间,剑式已由凌厉转为轻灵,“回风拂柳”的收势将出未出,剑尖微颤,凝而不发,蕴含着内敛的玄机与力量。
收势!
青锋于瞬息间稳稳滑入那古旧朴素的剑鞘之中,发出一声低沉悦耳的轻吟,仿佛龙潜深渊。
贾琰呼吸微促,胸中浊气随一剑收束尽数吐出,额头渗出薄汗。
“啪!啪!啪!”
清脆而缓慢的掌声突兀地从不远处的假山石后传来。
一道窈窕倩影扶着侍女(平儿)的手,缓缓步出竹林深处笼罩的阴影。
王熙凤依旧是一身耀目夺人的石榴红裙裾,那华丽繁复的裙摆此刻却毫不避讳地扫过被露水浸润得深重的草叶,染上一道道深色的湿痕。
更令人意外的是她今日的装扮——脂粉未施,素面朝天。
这张往日里惯用浓妆描摹艳色的脸庞,洗尽铅华后,竟透出一种近乎冷玉的晶莹质感。
乌发高绾,发髻间唯簪一支金累丝点翠凤凰钗。
那只展翅欲飞的凤凰精巧绝伦,口衔的珠串随着她的步伐在熹微晨光中轻轻摇曳,流泻下片片夺目的彩光。
这极致简约却无比贵重的饰物,非但未减她半分容光,反将她本就凌厉飞扬的眉眼神韵,衬得愈加孤高清绝,在未褪的晨雾里,竟别有一种洗去刻意雕琢后、纯粹而直慑人心的锐气!
仿佛一件剔透却无温的琉璃器,美得惊心动魄,也冷得拒人千里。
贾琰持剑回身,抱拳行礼,声音平稳无波:“凤嫂子。”
王熙凤唇边扬起一抹恰到好处的弧度,眸光流转,如同欣赏一件刚刚发现、值得玩味的新奇物件:
“可不是起了个大早么?全赖我们琰大爷这柄剑,”
她指尖虚点了一下贾琰腰间的剑鞘,“铮铮清鸣,隔着两重院子都听得真真儿的,想安寝片刻也不能够了。”
她伸出那只没染任何蔻丹、素净得在此时此地显得尤为奇特的手。
肌肤如玉,掌纹清晰,摊着一块素锦方帕。
帕子本身素净无香,只四角绣着几枝精致雅洁的缠枝牡丹,却与她腕间飘散出的沉水香息交织缠绕,无声地侵染着周遭的空气,编织出一张无形的细网。
“瞧瞧这一头的汗气,”她声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关怀,眼神却锐利如针,牢牢锁住贾琰的面容,带着不容置疑的探究,“擦擦?”
贾琰面沉似水,毫无波澜。
他没有去接那方香帕,只是面无表情地抬臂,用未持剑的手背在额头极迅速地一抹,动作干脆利落。
指节处沾上了几点晶莹的汗珠,在晨光下微微闪亮。
“晨寒露重,些许薄汗,不足挂齿。”他将沾汗的手背随意往身侧裤线上一擦,“不敢劳烦嫂子。”
拒绝之意干脆,却维持着表面的礼数。
王熙凤脸上的笑容未变,只是那双丹凤眼里的光似乎更亮了些,如同淬了冰的刀锋。
她收回摊开的素手,指尖捻着那方帕子,仿佛只是随手拂去一片虚无的尘埃。
气氛在无声的对峙中凝固了一瞬。
平儿有意无意道:“奶奶,时辰不早了,今儿还得去给老太太请安,听说宫里又赏了新东西下来,好像是……崔贵妃娘家那边送来的节礼,得先过去看看单子才好回话。”
还未待王熙凤反应,一个穿着靛蓝色布褂的小厮脚步匆匆地赶到,打破了这微妙的僵局。
他先是恭敬地向王熙凤行了礼,才转向贾琰:
“琰大爷,老爷刚从上房出来,命小的来请您进去一趟。说是有要事相商,是关于您……‘夺情应试’的旨意细则。”
贾琰眼神微凝,点头:“知道了。这便去。”
他转向王熙凤,“嫂子慢走,弟弟告退。”
他没再多看王熙凤一眼,紧了紧束在腰间束发的布带,转身随那小厮大步离去,身影很快消失在通往荣府正院的游廊拐角。
晨雾微散,阳光穿透竹叶,在王熙凤素面朝天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她望着贾琰消失的方向,缓缓收回目光,落在自己手中那方无人接受的、绣着精致牡丹的素锦帕子上,半晌,嘴角扯起一丝极淡、极冷的弧度。
她将帕子随意掷给身后的平儿:“沾了尘气了,拿去烧了罢。”
说罢,也扶着平儿的手,踩着那湿漉漉的裙摆,款款而去,只留下身后草丛里几片被碾碎的草叶。
贾政的书房弥漫着陈旧书香和浓重的墨味。
一排排高大的书架顶天立地,暗沉沉的色泽像凝固的暮色。
正对书案的主墙上,巨幅装裱的孔子行教图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整个房间。
图下条案上,一函函簇新未裁页、金丝楠木封函的《朱子集注》、《春秋正义》层层堆垛,像一座供人顶礼的偶像神龛。
贾政本人端坐在书案后宽大的太师椅上...案头堆叠着厚厚的账册和公文,几乎将他半个身子都埋在阴影里。
然而,那账册缝隙间赫然还压着一本被翻得卷了边角、污渍斑斑的坊间话本《玉娇梨传》。
“坐吧。”
见贾琰行礼毕,贾政抬了抬眼皮,指了下下手处的椅子,声音沉闷得如同敲击老木,
“陛下悯你年少失怙,特旨夺情准你入监,更期许你明年春闱下场应试,这是天大的恩典。”
他随手翻了翻案上一份盖着国子监印记的公文,
“入学的章程,都按规矩办妥了。叫你过来,一是确认此事,二则,三日后的入学考,多涉经史子集。”
他说着,枯瘦的手指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敬畏,下意识地拂过条案上那堆《朱子集注》上细腻平整的封函。
他顿了顿,端起手边早已凉透的参茶啜了一口,眉头习惯性地蹙着,
“读书明理,科举晋身,方是正途。不可依仗着几分家传的骑射底子,便整日舞枪弄棒,荒废了圣贤文章,惹人闲话,更辱没了陛下的期许……你可明白?”
他的话像是在陈述,又像是训诫,更像是一种带着厌烦的例行公事。
那双略显浑浊的眼睛透过茶盏升腾的稀薄水汽,审视着眼前这个沉默肃立的侄儿,试图从他的表情里搜寻到一丝可堪塑造的“孺子可教”之气。
贾琰垂眸而立,声音沉静,听不出情绪:“侄儿明白。定当谨记政叔教诲,潜心向学,不负皇恩,不负先祖之名。”
“嗯。”
贾政从鼻腔里发出一声听不出褒贬的轻哼,似乎对这个答案既无意外也谈不上满意。
“去吧。这几日便把国子监的课业理起来,莫要懈怠。”
他挥了挥手,目光已重新落回那叠账册之上,显然已无更多话可说。
贾琰依礼告退,转身步出这压抑窒闷的书房。
春日午后的阳光穿过镂空窗棂,照在回廊干净的金砖地上,竟刺得他微微眯了下眼。
冰冷的空气涌入肺腑,驱散了那股沉郁的书香墨臭,但贾政那句“舞枪弄棒”的评点,却如同薄刺般扎在心头。
他不发一言,脚步沉稳地沿着抄手游廊往梨香院方向走去。
途经府中家塾时,因想抄条近路避开可能遇到的闲人,便拐进了旁边一条相对僻静的夹道。
刚靠近家塾院门,一阵极其刺耳的声响便穿墙透壁而来!
“啪!啪!啪——!”
那是上好的竹木戒尺狠狠抽打在硬质桌面上发出的巨响!每一记都带着施刑者极大的恼恨和力气。
紧接着,便是一个老迈沙哑的声音在咆哮: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论语·述而》开篇尚且读不成句!还敢在老夫的课上酣睡流涎?!无知至此,顽劣至此!当老夫的戒尺是摆件不成!”
家塾的轩窗开着一条窄缝,恰好能瞥见里面的情形。
只见家塾最前方那张宽大的酸枝木书案后,贾宝玉正趴伏着。
半边脸颊死死压在一本翻开的《孟子》书页上,将那些方块字挤得扭曲变形。
压着书的脸上,赫然印着一片清晰的、半干未干的口水印渍,混杂着书卷的褶痕,显得格外邋遢不堪。
他被那剧烈的拍桌声和怒吼吓得浑身一个激灵,迷迷瞪瞪、极其不情愿地从书案上抬起头,睡眼惺忪,茫然地抹了把嘴边的口水丝,带着被吵醒的委屈和浓重的鼻音咕哝了一句,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了出来: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先生息怒啊……学生实、实不知《述而》书中所云为何物,若强要学生装作懂得作答,那岂不是……知而不言实为隐瞒?非欺师乎?”
这番似是而非、强词夺理却偏偏歪引圣贤的话,配上那张犹带睡痕口水印的脸,将负责教导他的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夫子气得几乎要当场背过气去!
手中戒尺捏得咯吱作响,一张老脸憋得紫红!
贾琰在窗外静立片刻,看着屋内这场闹剧,唇角极其短暂地、几乎微不可察地往上挑了一下。
他没有兴趣插手,更不会进去。
只默默收回目光,仿佛什么都没看见,悄然转身离去,脚步更快了几分。
身后的家塾里,老夫子那被气得倒抽气的声音和宝玉那半梦半醒的咕哝声,在清冷的春日午后,显得愈发荒诞刺耳。
他脚步未停,只将身后这片荒诞喧哗连同那声遥远书斋里的“圭臬”,统统抛在了门外清冷的空气中。
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他离去的背影上投下长长的、沉默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