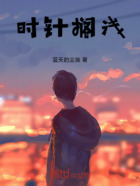
第3章 月考前的裂缝
粉笔灰在阳光里浮沉,刘老师的手在黑板上快速移动,画出一道陡峭的函数图像。
“这个区间内的极值点,用函数检验法……”
我死死盯着笔记本,笔尖悬在纸面上发抖,因为昨晚预习时,我花了两个小时才搞懂函数的定义,现在却被“平面转换”和“极值点”砸得头晕目眩。我现在感觉都听不懂,很艰难,前排的徐长乐已经抄完三页笔记,正在用铅笔给重点公式画星标——他的笔尖与黑板上的推导同步,仿佛大脑直接连通了刘老师的思维。
“周卿尘,上来解这道题。”
突然被点名时,我的后背瞬间渗出冷汗。讲台上,刘老师用三角板敲了敲黑板,一道最简单的求函数解析式的题目正张牙舞爪地瞪着我。
粉笔在掌心折断。我试图回忆例题的解题步骤,但脑海中只有零散的公式碎片。教室里响起窃窃私语,后排男生故意咳嗽:“超常发挥进来的嘛……”
“用定义法。”刘老师的声音冷得像冰。
当我颤抖着写下第一个积分符号时,下课铃响了。感觉整个人的心情都跌入了低谷,有点很难受。
夕阳把教室染成橘红色,我在《必刷题》上留下第三十四个问号。我在看一个函数题,但怎么都解不出来,感觉我看它们很亲切,但它们都不认识我。
“这道题需要构造辅助函数。徐长乐突然把草稿纸推过来,“看这里。”
他修长的手指划过纸面,像手术刀剖开混沌的迷雾。可当他把过程推到第三步时,我的思维就卡在了某个断层——就像军训时踢正步,明明知道动作要领,身体却跟不上节奏。
高乐佳抱着一摞作业本经过,扫了一眼我的草稿纸:“你连定义法都没记熟。”
我的耳尖发烫。她说的没错,我甚至分不清dx和dy哪个是自变量。高乐佳说,别着急,慢慢来,现在才高一,你可以的,周卿尘。
晚自习结束前,刘老师抱着一叠试卷走进来:“周测成绩出来了。”
教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抽气声。我死死盯着自己的卷子,61分,倒数第五。最后一道大题旁,刘老师用红笔写着:“步骤混乱,建议重学函数基础。”我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别人都很考的很好,只有自己惨不忍睹,估计肯定是倒数,很难受,心里也很懊悔,该怎么学呢?该怎么办呢?
徐长乐的卷子从桌角滑过来,145分的数字刺得我眼眶生疼。他的错题旁标注着三种解法,像在嘲笑我的无能。
刘老师的办公室堆满教案,窗台上养着一盆蔫头耷脑的绿萝。
“坐。”她推给我一沓泛黄的试卷,“这是我二十年前的学生做的题。”
发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像蜘蛛网。一道求极限的题目旁,有人用蓝钢笔写着:“试了七种方法都不对,但第八种成功了。”
“知道你为什么学不好吗?”刘老师摘下眼镜,“你总在第一步就放弃。”
她从抽屉里摸出铁盒,推来一颗薄荷糖——和军训时徐长乐给我的一模一样。
“从今天起,每天放学后补一小时基础。”
我含着薄荷糖,辛辣直冲脑门。窗外,操场上的梧桐树正在落叶,一片叶子粘在玻璃上,叶脉的纹路像极了数学卷上的辅助线。
徐长乐把餐盘推到角落,展开一张思维导图:“函数与方程是高中数学的脊椎。”
油渍溅在“数形结合”的枝干上,他用吸管蘸着番茄酱画抛物线:“你看,这就是二次函数根的分布……”
食堂阿姨擦着桌子经过,嘟囔道:“现在的学生吃饭都不安生。”
我突然发现他的笔记本秘密:每个章节页都贴着便利贴,正面是知识框架,背面是错题陷阱。当他讲到隐函数求导时,我的视线开始模糊——那些符号像军训时的正步口令,明明每个字都懂,连起来却让人窒息。
“听不懂?”他停下笔。
我盯着番茄酱画的坐标系,突然想起中考前夜:妈妈端着牛奶站在门口,我哭着撕掉模拟卷说“我做不到”。那时的眼泪,此刻又涌了上来。
周末的图书馆,我在角落发现一本《数学史话》。
笛卡尔在病床上发明坐标系的故事,被我折了三十六个角。当看到“费马定理”旁批注的“此处留白供后人思考”时,窗外的梧桐叶突然被风吹到书页上。
叶脉的网状结构,多像函数图像的切线簇。
“发什么呆?”徐长乐抽走我的书,往桌上拍了一本《初中数学总复习》,“先补完平方差公式。”
我咬着笔帽做因式分解,突然发现他在用手机录视频——镜头对准草稿纸,实时生成解题步骤。
“这是我自己写的程序。”他轻敲屏幕,“能捕捉笔迹轨迹,分析思维断点。”
密密麻麻的红线在屏幕上跳动,我的解题路径像迷途的蚂蚁,总在关键岔路绕圈。
“你总是跳过定理证明。”他指着一段循环轨迹,“就像正步走不练分解动作,直接练连贯动作。”
夕阳西沉时,我在图书馆的玻璃窗上哈气,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坐标系。徐长乐突然说:“你比上周多坚持了十五分钟。”
那一刻,我发现自己能看懂高乐佳错题本上的批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