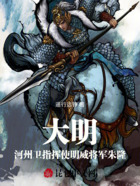
第4章 老骥伏枥
洪武十三年(1380年)霜降,河州卫衙署的老槐落尽最后一片枯叶。朱隆扶着窗台咳嗽,指节按在青砖上,那里还留着九年前初到河州时刻下的“定边”二字,如今已被风雨磨得浅淡。腰间旧伤在阴雨中抽痛——那是三年前巡视边墙时,被乃儿不花余党射中的一箭,箭头至今还嵌在胯骨里。
“大人,京里的驿使到了。”李安捧着漆盒进来,盒中躺着鎏金错银的虎符,“这次是徐皇后的懿旨,说皇子们开蒙,要调您回应天教骑射。”
朱隆盯着虎符上的云雷纹,忽然笑了:“皇上这是变着法儿让我致仕啊。”他接过李安递来的参片,茶汤里浮着几片吐蕃红花,“九年了,河州的边墙从土坯换成砖石,茶马司的金牌发了十七道,蕃汉通婚的册子记了三大本……”他忽然按住李安的手,“可你看这积石山后,乃儿不花的斥候还在晃荡,旺嘉丹增的孙子去年又在草场埋了诅咒的牦牛骨——”
“大人,您都五十八岁了!”李安的声音带着哽咽,“去年巡查二十四关,您在马上颠簸七日,回来吐了半盆血——”他忽然跪下,头顶的头盔磕在砖地上,“末将不想看您像邓愈将军那样,累死在疆场上!”
朱隆扶起李安,望着窗外正在操练的“蕃汉混成营”:前排汉兵持弩,后排吐蕃骑兵握刀,口号声混着藏语的呼喝。他忽然想起长子朱芾十岁时,在应天学宫背《孙子兵法》,背到“兵贵胜,不贵久”时,眨着眼睛问:“父亲在河州,算不算‘久’?”如今朱芾已十九岁,随他在河州历练五年,能说流利的吐蕃语,骑术比嵬名阿旺的儿子还精湛。
次日卯时,朱隆带着朱芾走进吐蕃帐群。旺嘉丹增的毡帐里,老酋长正在用汉人的算盘拨弄青稞——那是朱芾去年送的礼物。“汉人官要走了?”老酋长的手指停在“八”字档上,“我孙子说,你走了,新官会砍了我们的经幡?”
朱隆让朱芾跪下,双手奉上象征河州卫的青铜印信:“这是我儿朱芾,以后河州的事,他听您老的,也请您老听他的。”他指着朱芾腰间的九环刀——那是他用自己的柳叶刀,换了嵬名阿旺祖传的吐蕃佩刀改铸的,刀柄缠着汉藏两族的彩绳,“他比我狠,也比我细,去年在叠州,他不用一兵一卒,靠二十车盐巴换得三部落归附。”
旺嘉丹增忽然笑了,缺了门牙的嘴里呵出白气:“去年他在我帐里,喝了三碗青稞酒不醉,倒把我三个儿子灌得爬不起来——”他拍了拍朱芾的肩膀,“汉家的‘虎父无犬子’,说的就是你们吧?”
离任前一日,河州百姓倾城而出。汉民捧着刚蒸的锅盔,吐蕃人献上哈达,就连僧纲司的喇嘛也抬着酥油灯送行。朱隆骑马行至积石关,忽然见关墙上新刻了行藏文——是嵬名多吉带着牧民连夜凿的,译过来是“朱公去,山不崩,水长流”。
“父亲,您看。”朱芾指着远处的烽燧,那里升起的不是警报的黑烟,而是牧民煨桑的白烟,“他们终于知道,烽烟不只是战争的信号,也能是祈福的香火。”
朱隆摸着马鞍上的凹痕——那是九年来他亲手打磨的印记,忽然将印信递给朱芾:“记住,河州的刀,不是用来砍人的,是用来切茶、割青稞、修边墙的。”他望向东方,应天的方向隐在云雾里,“若有一日朝廷要变茶马法,你就把这印信砸在金銮殿上——”
“父亲!”朱芾惊惶跪地,却见父亲眼中闪着泪光。这是他第一次见父亲流泪,上一次还是祖母去世时。
是夜,朱隆在衙署整理文书,发现夹在《河州志》里的一片吐蕃氆氇,上面用藏文绣着“平安”。那是旺嘉丹增的女儿、他的儿媳卓玛绣的——五年前,他促成了朱芾与卓玛的婚姻,让汉家指挥使与吐蕃酋长结为亲家。烛花爆响时,他忽然在文牒上补了句:“蕃汉通婚者,免三年赋税;所生子女,可入卫学选读汉藏两文。”
黎明启程时,朱隆特意绕开了夹道的百姓。他骑在马上,望着渐渐缩小的卫城,忽然觉得自己像一粒融进大夏河的雪——曾经棱角分明,如今却化作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李安跟在身后,背着他的行囊,里面除了兵书,还有半罐吐蕃的青盐、汉商送的蒙山茶,以及二十封百姓的书信。
行至三十里外的歇马坡,朱隆忽然勒住马。山风送来河州城的晨钟,混着远处传来的马蹄声——是嵬名阿旺带着马队追来,马背上驮着三匹最精良的河曲马,马鬃上系着汉藏两色的丝带。
“朱指挥,”嵬名阿旺翻身下马,将马缰塞进朱隆手里,“这马,替我们去看看汉人的皇帝。”他忽然压低声音,“若有蒙古人再来挑事,我儿子会带着吐蕃的刀,比你当年杀得更狠。”
朱隆抚过马鬃,忽然笑道:“记住,刀要杀该杀的人,茶要敬该敬的客。”他转头对朱芾说:“明日起,每月初一,你带汉家匠人去蕃帐教冶铁;十五,让吐蕃骑士来卫城教骑射。”他望向层叠的山峦,朝阳正从雪顶升起,“治边如熬茶,急不得,要慢慢煨,才能熬出香味。”
马蹄声渐远,河州卫的飞檐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朱隆摸了摸腰间的九环刀——此刻它不再属于河州卫指挥使,却永远刻着这片土地的纹路。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而朱芾的故事,正随着第一缕阳光,在积石山麓悄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