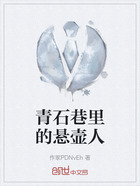
第1章 青石板上的脉息
柴油机的轰鸣撕开清晨的雾霭,22路公交车碾过青阳县马山镇的青石板路,车厢里此起彼伏的颠簸声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王砚的帆布包随着摇晃撞在膝盖上,里头沉甸甸的《伤寒论》硌得生疼,书页间夹着的干枯艾草叶窸窣作响,那是父亲三天前特意从老宅药园摘的。手机在裤兜里震动,屏幕亮起父亲发来的语音:“到了先找张院长,他年轻时和我在山里采过七年药。“
他低头看着录取通知书,“马山镇卫生院“几个字被反复摩挲得发毛。出发前的深夜,父亲戴着老花镜坐在八仙桌前,用狼毫在宣纸上写“悬壶济世“,墨迹未干就被王砚抢过叠进行李箱。“别总惦记家里的药园,“父亲往他包里塞了包自制的驱蚊香囊,“山里湿气重,记得每天喝碗薏米粥。“
公交车猛地刹车,王砚的额头撞上前排座椅。抬眼望去,斑驳的牌坊上“马山镇“三个大字被风雨侵蚀得缺角少捺,山雾像揉碎的棉絮,裹着潮湿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远处山坳间,几缕炊烟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恍如《黄帝内经》里描绘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他深吸一口气,帆布包的肩带已经在肩头勒出红痕,父亲的叮嘱却在耳边愈发清晰:“基层是中医的根,别嫌苦。“
卫生院的青砖楼被爬山虎缠得严严实实,铁门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消毒水混着陈年艾草的气息扑面而来,墙角堆着半人高的草药编织袋,标签上的字迹被雨水洇得难以辨认。值班室的木门虚掩着,戴圆框眼镜的张院长正用搪瓷缸子泡浓茶,茶叶在水面上打着旋儿,袅袅热气在晨光里凝成细小的水珠。
“是老王家的小子?“张院长推了推下滑的眼镜,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笑意,“你爸今早还打电话,说你背《金匮要略》能倒着来。“他往搪瓷缸里续了些热水,水汽模糊了镜片,“咱们中医科就剩个老中医上个月退休,现在整个镇的中药摊子,都得靠你撑着了。“话音未落,远处传来老式座钟的报时声,沉闷的钟鸣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
诊室的阳光斜斜切过褪色的白漆窗台,案头的老式座钟停在九点十七分,铜制的钟摆上结着细密的蛛网。王砚轻轻擦去脉枕上的灰尘,刚把《濒湖脉学》摆上桌面,手机又震动起来。父亲发来段语音,背景里传来捣药臼的咚咚声:“后院药圃的薄荷该浇水了,还有,遇到急症别慌,先摸脉......“
突然,走廊传来重物坠地的闷响,紧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哭喊:“来人啊!救命!“王砚冲出门时,看见个白发老汉瘫坐在墙根,嘴角歪斜,浑浊的涎水顺着下巴滴落,手里的搪瓷杯摔得粉碎,枸杞混着茶水在青石板上蜿蜒成暗红色的溪流。老人的老伴跪在一旁,布满老茧的手死死攥着他的衣角,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绝望。
“中风!“王砚膝盖重重磕在冰凉的地面,指尖搭上老人的寸口脉。脉象洪大弦长,像暴涨的河水拍打着堤岸,指下的脉动带着令人不安的躁动。他扯开老人领口,瞥见墙上的急救箱,父亲的声音突然在脑海炸响:“闭证急救,先针百会!“消毒棉签擦过百会穴时,张院长举着硝酸甘油冲了进来:“快叫救护车!这种情况必须送县医院!“
银针在手背上顿了顿,王砚想起上周在家演练急救时,父亲把着他的手腕调整进针角度:“针要稳,心要定。“当第一根银针刺入人中穴时,老人喉间突然发出粗重的喘息,扭曲的面容微微舒展。紧接着,风池、内关、足三里......银针如飞,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光。汗珠顺着他的下颌滴落,在白大褂上晕开深色的痕迹。
“中医急救,到底是慢半拍......“张院长的叹息混着救护车的鸣笛声,在走廊里久久回荡。王砚看着担架床远去,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不停。父亲连发来三条语音:“做得好!观察舌象!别忘了让西医做CT!“最后还附了张照片——老宅药园新栽的半枝莲,在阳光下开得正盛。
暮色漫进中药房时,王砚独自坐在药斗前。当归的辛香混着樟脑气息萦绕鼻尖,他翻开白天的病历本,钢笔尖悬在“中风闭证“四个字上方迟迟未落。窗外,后院的药圃里,几株野菊花在风里轻轻摇晃,花瓣上的露水折射着最后一丝天光。手机再次震动,这次是视频通话请求,父亲举着《千金方》出现在屏幕里:“看看这个续命汤的加减法,明天我把家里的验方本寄给你......“
王砚摩挲着泛黄的书页,看着屏幕里父亲鬓角的白发,忽然想起小时候跟在他身后采药的光景。那时总嫌山路难走,如今却觉得,父亲走过的每一步,都在为他铺就这条青石路上的中医之道。他摸出备忘录,借着台灯昏黄的光,郑重写下:“青石路上的第一味药,是传承。“窗外,山雾又起,裹着若有若无的药香,漫过卫生院斑驳的砖墙。而在百里外的老宅,父亲正对着药园的月光,将新采的草药仔细晾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