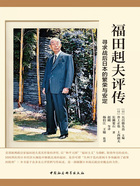
一 故乡
(一)金古的粟米饭
在江户时代,沿着穿越上州和越后的三国街道,在接近高崎的地方,有一条叫金古宿的住宿街。到明治初年为止,当地有将近30家的旅馆和茶室,是一条颇具规模的住宿街。
与金古宿的西南相接的农村地带,有一个叫足门的村庄。金古宿是幕府的自领地,足门村则归距离金古宿往北30公里的沼田藩管辖。金古宿和足门村到江户时代为止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领主,但是伴随明治市制、町村制的实施(1889年),合并成为金古町。
福田诞生于金古町成立十六年后的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正值日俄战争的时期。
福田家拥有30町步(约30公顷)的土地,是金古町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当时的金古町有520户,人口约2300人。虽然之前的金古宿时代的旅馆已经改换门庭,继续进行着商业活动,但从人口比例而言,绝大多数都是农户。这些农家的平均耕地为七八反(10反约为1町),也有很多没有耕地的长工。从拥有土地的面积来看,福田家在当地可谓首屈一指。
但是,这些土地也有很大的缺陷。原因是这一带的土地属于榛名山火山石灰岩地带,因为水利设施不好而不能种米,平时只能收割一些诸如杂粮类的粟米以及长茄子之类的农作物。在以粮食收成为要的年代,凡是收成不好的地区,都被视作落后的农村。准确地说,金古町虽然也能收割旱稻,但是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欠佳。就算是拥有大量的土地,跟利根川周围的水田地带相比,其价值连它们的一半都不到。
在《金古町志》中,福田回顾幼时曾经写下了以下的文字:[2]
“金古的粟米饭,足门的长茄子”,对小时候的农村有过这样的记忆。尽管离东边有着丰富水资源的利根川只有不到一里地,在水利设施不发达的年代,周围丰富的水源并未能给这一带带来恩惠。缺乏水田的金田町,绝大部分的土地种植了桑树、大麦、旱稻和蔬菜,中间夹杂有一些橡树林,在橡树林中又有很多古坟。已经逝去的父亲出生的地方就有一片橡树林,它们一直延续到榛名山麓脚下(略)。
水利工程需要大笔资金。金古町从明治时代开始,就不断向县以及中央政府申请资助。但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才得到批复。其后,群马县将利根川引水工程列入其水利规划,1960年5月终于得以竣工。
福田在《金古町志》中写下其对金古町的回忆,是在工程竣工三年后的事情,“金古的粟米饭”也成了往事,在《金古町志》中福田还写下了以下的文字:
那片橡树林逐渐被砍伐一空,古坟也慢慢消失,那个村庄也变成了普通的农村,伴随水资源被引入乡里,新开的农田不断增加,想吃的粟米饭没有了,长茄子也不再是当地的名产了。
福田用他平淡独特的笔法描述了对故乡的怀念和乡愁。金古町在1955年3月与其他村落合并成为群马町,2006年(平成十八年)1月,并入高崎市至今。
(二)法国蚕桑的毁灭
榛名山又被称为榛名富士,作为观光胜地闻名遐迩的榛名湖就是它的火口湖。榛名湖火山喷发大概是在6世纪的时候。在6世纪初以及中期,有过两次大的火山喷发。火山喷发产生的大量的火山灰和火山石,布满了周围一带。连距离火山顶15公里外的村庄和群落,也都埋没在两米高度的火山灰里。
在群马县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火山。在国定忠次的《任侠传》里描写的赤城山是位于群马县东北部的大火山。跟榛名山一样有名,它们是位于上州平野北部的两大火山。
同时,在长野县境内的浅间山从16世纪以后直至20世纪为止,火山经常喷发,火山灰覆盖了从上州到信州,以及关东一带的地域,导致了周围地带的农作物颗粒无收,爆发了悲惨的大饥荒。特别是江户时代爆发的天明火山喷发,一直持续了五年之久,火山爆发造成了大饥荒,在上州和信州,有很多类似金古町这样的区域无法种植水稻。
但是,上州和信州在幕末时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革,起因是佩里(Matthew Perry)黑船的到来以及神奈川和横滨的门户开放。
期待因横滨港的开放而能一本万利的欧美商人络绎不绝地来到横滨,其中最为活跃的是进行生丝及绢丝物品的贸易商人。
特别是作为欧洲最大的养蚕地域的法国,由于家蚕易患的两大病状——微粒子病和软化病的蔓延,几乎所有的产地都受到了影响。从1855年开始,疫情一直延续到当时也依然不见好转。
欧美在产业革命以后,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富裕阶层对丝绸的需求急剧增长。但是,欧洲蚕蛹的产量骤减使供给发生了问题,导致绢丝的价格居高不下。
由于上述原因,欧美各国只能在法国以外的地区寻找绢以及生丝的产地。因为中国是养蚕的发源地,他们首先关注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却因为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动乱而政局不稳。
因此,他们又将目光转移到了日本。日本在公元2世纪的前期从中国得到了养蚕技术,比卑弥呼的时代稍早一些。其后,养蚕技术在日本生根发芽,尤其在江户时代中叶以后,产地急速扩展。因为绢织物非常昂贵,在古代和中世纪,只是一小部分贵族的特需品。但是,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富裕阶层快速增长,上层武士以及富商大贾的需求增加。随之上州及信州的粮农也都转而成为蚕农。[3]
养蚕必不可缺的是桑叶,而火山的土地有利于桑树的生长。因此,当地的养蚕业也逐渐变得引人注目。但是,从事养蚕的农家都是一些零散农户,他们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桑田经营。也因为如此,当时的农家主要还是依靠野生桑树,产量即便有所提高也终有限度。当时的日本也正值幕末维新的动乱时期,也不能被称为安定社会。
即便这样,各国的贸易商也是在跟中国市场比较后选择了日本,他们派了很多专家到日本各地考察。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法国考察团。他们前后两次访问上州和信州、甲州以及越后等地,并向本国提交了详细的报告。[4]
考察团第二次的调查是在1870年(明治三年)进行的。考察团里有一名叫保罗·布鲁纳(Paul Brunat)的养蚕工程师在他的报告书里做了以下的陈述:“如果在日本建设现代化的生丝工厂,(拥有像榛名山那样适合养蚕的山地的)上州富冈地区是最合适的”。得知保罗报告的明治政府立刻聘用了保罗,仅用两年时间,即1872年,就在富冈建成日本第一家国营现代化生丝工厂。富冈生丝工厂在2014年(平成二十六年)正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其后不久,日本的商人们从外国贸易商那里接单,为数众多的商人或代理人为了购买生丝在全国各地奔忙。他们告诉蚕农说:“生丝有多少就会收多少”。因为外国商人有无限量的需求。听到他们这么说,粮农们倍感欣喜。金古町的福田家也不例外,他们带头大规模改田植桑。
(三)象山的徒孙
福田家的祖先在战国时代上杉谦信与北条氏康争夺关东地区霸权的时候,据说是上杉在群马所筑众多小城堡中一个的家老。但是因为没有经过文献考据,只是限于传闻。
可考据且有确切记载的资料直到幕末才有。在介绍上州剑士的《上毛剑士》中,有一位被记录在册的足门村富农的长子,他就是年轻时代的福田的祖父——幸助。[5]
在江户时代末期,由于政局不稳,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也动摇了。农民阶层也出现了大量练习剑术的人物,与此同时,练习剑术的道场也纷纷出现。
前来学习的人群主要由生活条件较为宽裕的富农家的老二、老三构成。这不仅是为了可以在动乱时代护身,也因为农民阶层期待在政局不稳的时代,通过成为剑术名家而取代武士阶层。
在这些农民剑士中最为有名的是,出生于武藏国多摩的天然理心流的近藤勇以及土方岁三。在幕府召集浪士队的时候,这些虽然出身农家但是对自己的剑术颇有自信的年轻人积极响应,到了京都后当选了新撰组的队长或是队副,成为当时的有名人物。根据当时的剑术史的记载,特别是在幕府的管辖区域的关东地区,像近藤这样优秀的农民剑士还是挺多的。[6]
在他们中间,最为有名的是上州金古宿的富农中泽家的老四中泽清忠,他从小就身强体壮,又精通中国古典,成年后即往江户游学。
到江户后,中泽清忠又进入小野派一刀流的中西道场拜师学艺,迅速提高了武艺,而且只用短短几年就得到真传。他那时候的师兄弟里有一位叫千叶周作的人,后来成为坂本龙马的剑术老师。
中泽清忠结束了在江户的修行后又周游列国、交流剑术,最终回到故乡创立了一家名为英隆馆的道场。其后不久,信浓松代藩通过同属上州的沼田藩,邀请他出任剑术教头。沼田藩与松代藩的共同祖先是真田氏,所以他们之间有着密切交流。[7]
在家排行老四的中泽清忠从小就成为金古宿邻村的足门村一户姓间庭家的养子。而足门村如同前文所述属于沼田藩管辖。因此,可以推测,正是因为沼田藩主向松代藩主推荐,中泽清忠同时也成为松代藩的剑术教头。[8]
福田赳夫的祖父——幸助正是在那个时候,成为寄宿在中泽清忠的松代藩中泽道场中的入室弟子。福田幸助作为福田平四郎家的长子,生于1850年(嘉永三年)。据传幸助自幼聪明伶俐,因此6岁的时候就成了中泽的入室弟子。
将幸助带去遥远的松代的是他的祖父藤兵卫。藤兵卫也是中泽的好友。藤兵卫认为,为了将幸助培养为一个优秀的人物,除了投身中泽门下以外别无选择。幸助也没有辜负他祖父的厚望,在中泽门下经历了各种磨炼后,很快成为一名干练之才。
出山后的幸助不仅剑术超群,学问也出类拔萃。还考入刚开设不久的“象山塾”,而当时的塾长就是幕末最著名的开明人士佐久间象山。
象山虽然只是松代藩的低级武士,但是他从青年时代就饱读诗书,在获悉鸦片战争的情报后,将关注点放到国防研究,还特意前往江户学习西洋炮术和当时流行的兰学。与此同时,他又提倡“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主张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象山把这样的观点灌输给了吉田松阴、胜海舟、坂本龙马等人,“知己知彼”(了解世界,了解日本)是象山教育的出发点。同样,幸助也把这样的理念传输给自己的孙子福田赳夫。
吉田松阴在佩里来航的时候,曾想坐船偷渡前往美国学习,但是因为被发现而未能成行。象山也受此牵连被赶出江户回到松代蛰居。幸助正是在象山蛰居期间考入象山塾学习的。
聪明伶俐的幸助在象山塾被称为神童。而很多年以后,幼年的赳夫从小跟着祖父学习汉文,同时也对社会构造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毫无疑问,幸助将自己在象山塾学到的各种知识进行了倾心传授,从这个角度来说,福田也能被视为象山的徒孙。
从中泽道场及象山塾学习结束回到故乡足门村的幸助当时已经20周岁,时值明治维新后的1870年(明治三年)的秋天。虽然他在外游学学到很多本领,但是当时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光凭剑术已经无法谋生。因此,幸助回家后全身心投入了农业,与当地的伙伴一起为养蚕业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887年(明治十年)的《足门村志》载有足门与金古两地的比较数据:[9]居民人数,金古1235人,足门531人。从人口看足门不及金古的一半。但是,足门的蚕茧产量、生丝产量、绢产量却分别是金古的1.6倍、2.2倍、3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作为足门富农的福田家为此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这也体现出为养蚕业发展呕心沥血的福田幸助的功劳。以养蚕业的高度发展为背景,金古和足门的人口迅速增长,从福田赳夫出生的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的2300人,到大正年间已经有了25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