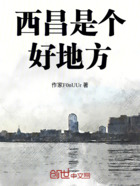
第5章 火把灼灼 浓情升温
七月末的凉山州像被泼了墨,云层压得极低。我攥着车票挤下绿皮火车时,迎面撞见站台上几个彝族汉子正搬运成捆的松木。干燥的松脂香混着站前广场飘来的烤荞麦饼香气,提醒我这座卫星城即将迎来它最炽烈的夜晚。
阿依的银耳坠在人群里晃出碎星般的光。这个皮肤黝黑的彝族姑娘接过我的背包时,指尖还沾着靛蓝的扎染颜料。“来得正好,“她指向远处腾起青烟的邛海湿地,“寨子里的阿嬷们已经开始熬松油了。“
我们穿过老城区的石板路,街边木楼垂下的火麻绳在风里荡秋千。五金店门口,戴英雄结的老者正用柴刀劈开整根的青冈木,木屑飞溅处飘起新鲜植物的腥甜。阿依说这是制作“都载“——火把节主火把的原料,要选十年以上的老树芯,烧起来才有清冽的松香。
城郊的吉瓦寨飘着蓝雾。七十岁的阿普爷爷坐在火塘边,正用鸡毛蘸着熬化的松脂往火把上涂抹。见我凑近,老人布满裂痕的手突然抓住我的腕子:“女娃,来试试。“浸透松油的麻布条缠上木棍时,指尖传来的黏稠触感让我想起外婆熬的麦芽糖。
暮色初临时分,月城广场已成了银饰的海洋。穿查尔瓦的姑娘们头顶的荷叶边随舞步翻飞,环佩叮当声里,我数见她们百褶裙上绣着的火镰纹样——那是彝族迁徙史诗《勒俄特依》里记载的,先祖用火镰击石取火的神迹。
忽然有牛角号穿透暮霭。十二位毕摩摇动铜铃登上祭坛,他们手中经卷的羊皮封面在火光里泛着琥珀色。当主祭将火把伸向三米高的柴堆时,我听见身后有老妪用彝语轻诵:“阿普多莫(火神)来了......“
第一簇火苗窜起的刹那,十万支火把次第绽放。阿依把点燃的松明子塞进我手里,热浪扑上面颊的瞬间,我看见无数光点在邛海的水面跳跃。穿天茄紫披毡的少女们开始旋转,百褶裙旋成燃烧的牵牛花,小伙子们的月琴声里裹着火星迸溅的噼啪。
“莫让火把低过腰!“人潮涌动时,阿依在我耳边喊。原来举火的高度关乎来年运势,我慌忙将快要垂落的松明子举过头顶,却烫着了前面小伙子的英雄结。他转身时,我看见火光在他银质额饰上淌成一条河。
深夜的火把巡游像流动的熔岩。我们跟着队伍从航天大道拐进建昌巷,檐角挂着的铜铃在热浪里叮咚作响。烤洋芋的焦香从某个院落飘出时,戴虎头帽的孩童正举着微型火把追逐嬉闹,他们鞋尖的绣球在石板路上滚出细碎的光痕。
当最后一批火把投入邛海,水面浮起万千星子。阿依说这是送火神归位,那些渐渐暗去的红点会化作来年春耕时的雨水。我们踩着露水往寨子走时,听见守夜的老人们仍在火塘边吟唱:“火是衣裳暖身,火是刀耕辟土......“
晨雾未散,我被寨口的喧哗惊醒。斗牛场里,两头扎着红绸的壮硕公牛正以犄角相抵,牛尾扬起的尘土在朝阳里闪着金粉。摔跤场边,少女们将索玛花抛向获胜的勇士,有个戴鹰爪耳环的青年接花时,我看见他绑腿上的火纹刺绣还在泛着昨夜的火光。
阿普爷爷在火塘边煨着苦荞茶,茶罐里飘出的烟霭爬上梁柱间的腊肉。“从前啊,“老人用火钳拨弄炭块,“我们的火把要烧七天七夜。“炭火明灭间,他讲起那些随火种迁徙的岁月:马帮如何用火把在雪山指路,毕摩怎样借火光占卜丰年,还有那个被记载在《玛牧特依》里的传说——勇敢的牧羊人用火把驱散冰魔,让春天重回大凉山。
临别那日,阿依送我一支未点燃的“都载“。松脂凝固成琥珀色的泪滴,青冈木纹路里还封存着阳光的温度。火车启动时,我看见远处山脊线上有迟归的火把在游动,像诸神遗落在人间的星子,又像古老部族依然跳动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