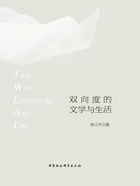
当家庭关系的面纱被撕裂
都说家庭是心灵的避风港,是吗?
人类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隐秘处污渍斑斑的华丽丽的袍子。平日里你餍足于这华丽的外在,“岁月静好”,一切相安无事。而一旦得以窥见内里的肮脏,你会怎样?
战争的风云,时代的剧变,谋杀案件的可怖……凡此种种,似乎都比不过和风细雨的家庭里那种最无事的表象下隐藏的悲哀来得更深入骨髓。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留下了一些老朽甚至如秃鹫一般的肖像照片,却被誉为是“法国王冠上最美丽的珍珠”。他之所以成为国家的“珍珠”,并非是因为讴歌了故土的大好河山,而是不惮于将最锐利的针砭刺入那个国家的每个细胞中去,对这些微小细胞毫不留情地抽丝剥茧,整个社会阶层,整个国家体制,都被解剖得入木三分,令人不寒而栗。
他是一个敢于直面最残酷的真相的人。最残酷的真相,莫过于打碎人们的幻想,告诉他们在貌似最坚固的堡垒中,却是有着最易被击破的角落。令人叹惋的真相,正是我们对于家庭、对于血脉亲情、对于姻缘爱情的信仰,恐怕仅仅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而已——在很多时刻。你以为你是生活在一座美轮美奂的伊甸园,风暴来临的时候,你才恍悟自己一直身处一片“爱的荒漠”。
并不似莫里亚克那般拼了全力要撕烂家庭的虚伪面纱,易卜生只是浮掠几笔,却也已深深地把利针扎进了温情的肉里。《玩偶之家》,或者说是《泥娃娃的房子》(英译A Doll’s House),简直就是一个恐怖故事,丈夫海尔茂真人与假面之间的巨大落差,真真是让人“活见了鬼”!总觉得“泥娃娃的房子”这个意象更形象、更准确地传达了这个故事的内涵。这个故事可以说就是写一栋大房子是怎么变得越来越逼仄,而一个泥娃娃又是怎样有了自主的呼吸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过程。房子再大再舒适,竟然渐渐地没有了主妇的容身之地,这着实令人心寒;而泥娃娃浑浑噩噩数十年,从父亲家的泥娃娃做到丈夫家的泥娃娃,终于一朝梦醒,毅然决然要脱胎换骨,又不能不说是一出掺杂了失落与绝望的喜剧。类似于鲁迅比喻当中的铁屋里的人,昏沉沉将要死灭,是该唤醒呢还是唤醒呢还是唤醒呢?易卜生当然是要唤醒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娜拉归还了戒指,自己对自己宣布了自由,迈出家门之后的路固然崎岖艰涩,却也未必如鲁迅所预言的那样悲观,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或者死掉。伟大的莎翁,放言“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数个世纪过去,Frailty和Woman的对应,依然余音袅袅,不知合了多少人的心意,然而我们的娜拉,却要打碎这魔咒了,尽管她只能净身出户,尽管她已在家庭的樊笼里把一腔热情和才能都献给了她的“床畔陌生人”和俨然已演变为新的泥娃娃的孩子们。她可以不走吗?她隐秘的债务眼看就要还清了,她一向崇拜的丈夫眼看就要升官发财了……她不能。“留下来的娜拉”阿尔文太太已经以身试法,证明了此路不通。阿尔文太太也曾何其果敢,结婚不到一年就从家里跑了出去。但她终又折翼而返,是因为听从了糊涂牧师的规劝,打算“死守妇道”。死守的结局绝不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只是在死路一条中被无数的鬼所缠绕,终至窒息。这便是《群鬼》,是比《玩偶之家》更凄惨的人生选择。在假面揭穿之后,与其劳神地维系,不如放自己一条生路……阿尔文太太不明白这个道理,娜拉明白……面对娜拉离去的决绝,海尔茂方才知道悔过:咱们俩都得改变到什么样子?意识到“屋子空了,她走了”的瞬间,海尔茂心里闪出新的希望,他开始祈望“奇迹中的奇迹”,这是他要改过的讯号,也是将来他们夫妻能够复合的前提。而从前的娜拉,那个依偎在丈夫身边言听计从的“小松鼠”“小鸟儿”“小宝贝”,是没有个人尊严可言的,她只是海尔茂预设中谦卑的驯服工具而已。因此,关于“化装舞会上穿什么衣服跳什么舞”这样的芝麻绿豆琐事,都要丈夫来下旨。娜拉投其所好去跳土风舞这种曲意逢迎的举动,海尔茂完全不以为意。他拒绝向娜拉表示自己的感谢,一个女人,去做男人的摆设,竟然是义不容辞理所应当的。
易卜生是个“伟大的问号”,他不愿意去作答诸如娜拉走后会怎样,娜拉不走又会怎样这样的问题。他揭开了疮疤,就转身离去。但他实际也已经作答,用其他的相关作品,用互文的隐晦方式。
我钦佩于这个家常故事中的挣扎。一幕幕的日常场景,有圣诞的欢愉,有盛会上漂亮的妆扮,有永远的备胎的忠诚守护,有三个长着“苹果和玫瑰花般”小脸的孩子。娜拉完全可以低头,完全可以在寂寥的大房子里继续优渥的生活。家务事里无是非,不须讲原则,最难得是糊涂——这被奉为经营婚姻的金科玉律——只是我想这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言,而真相则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有原则的,即使有个人的立场作祟——但那会是对那个个人来说的原则,而并非没有。固然相当多的时刻,在家庭这样一种特殊的物理心理空间内,是可以选择无视的。但当大风暴来临之际,亲人之间的刻意相疏,会不会令人齿冷、肝颤?
我常常穿越历史的风口,步入上世纪那个黑色幽默从不落幕的荒诞时期,看到那一纸纸“断绝关系”“划清界限”的声明,那就是一声声的惊雷,要劈裂我们愚妄地执着于“血浓于水”的狂想。那是严重化的娜拉海尔茂事件,面对比娜拉伪造签名的违法事件更严重的态势,海尔茂们的反应千古不变地一律都是明哲保身;面对比“同林鸟夫妻关系”更切近的直系血亲,古希腊人为蒙冤的血缘至亲所背负的雪耻义务早已烟消云散,现代庸人只剩下了仓皇的“各自飞”。与生俱来的亲情,到底有多可贵?莫里亚克让苔蕾丝∙德斯盖鲁(《苔蕾丝·德斯盖鲁》)去寻找“真正的亲人”——与那与生俱来或法律意义上的亲情不同的——精神上的亲人。精神上的契合,才是真正的亲切。卡夫卡也早已参破那份执信,他说,最亲的人反而是最大的羁绊。因此,不要问他为什么三度悔婚了吧。
诚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阅读名家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会使我们变成更好的公民。经典并不能教人去做一个“好人”,可是难道是要教我们做坏人么?我想,应当是要做一个丰富的人吧。读得越多,你思想的旷野越大,你的呼唤可能就会愈加辽远。这种呼唤,无关道德,无关教条,无关切身的俗务。
因此,尽管我感恩我拥有可亲的家人,我依然深爱着热衷于揭疮疤的莫里亚克,深爱着让娜拉留下悲怆背影的易卜生。波澜不惊的一潭水,是当不起艳羡的死水,而四面漏水充满裂缝的人生,未尝不是完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