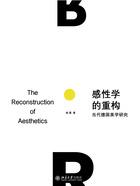
第一节
“显现”的含义与构架
因此就有了“显现”这一概念的诞生。“显现”,简而言之,就是“诸显象间的游戏”[48]。而“显象”,则是“可以通过概念来区分的感性特征”[49]。显现这个概念展示了泽尔美学应对挑战的基本策略,也表明了他美学的基本立场。既然传统美学思路不足以应对挑战,那么就应该抛弃。这种传统美学思路,泽尔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聚焦于“实际”(Sosein)或者“存在”(Sein),认为要为了更高的存在之真,抛弃虚幻的现象界;另一条是聚焦于“假象”(Schein),承认经验世界的虚幻性,但不是超越与抛弃,而是投身。前者是柏拉图反艺术的思路,后者是反柏拉图主义者,比如尼采的思路。无论怎样,二者都是对感性现实自身可靠性的不信任。泽尔认为审美活动既不是诉诸存在意义上的事实性,也不是诉诸超越感性实际的幻象世界,而是建基于经验活动本身,泽尔称之为一种“事态”(或者叫“发生”)[50]——无论审美对象还是审美感知,都融入了这样一个显现“事态”的事实性中。这种显现事态不具有也无须具有存在意义上的客观性,但具有经验意义上的事实性。简而言之,泽尔的焦点在于一个动作,一个大写的动词“Ers-cheinen”(显现)。如果我们把以往的美学叫“静态美学”,那么,不妨称泽尔的美学为“动态美学”;如果我们把以往的美学叫“事件(事物)美学”,不妨称泽尔的美学为“事态美学”;如果我们把以往的美学叫“空间美学”,那么,不妨称泽尔的美学为“时间美学”。
审美的时间性是泽尔整个美学的焦点。这样一种时间性必然首先是“当下性”。如果我们把“过去”与“未来”所撑起的那种稳定的持续性时间看作对时间的某种空间性想象,那么,真正的时间性其实只有瞬间时间,时间性的特征就只是流逝。唯一能在感知中浮现的只有“当下”,其他都是概念与想象的构造。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对人类认识与实践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在世的时间性维度——更确切地说,当下性维度——的聚焦。自然,我们无往而不处于“当下”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生存之开展是对当下的遗忘,只有在审美显现的事态中,我们对“当下”有所觉悟,心无旁骛地对“当下”的“当下性”进行观照。
因此,“显现”概念是与“当下”概念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诸显象间的游戏”,它有一种“瞬时性”和“同时性”特征,瞬时性意味着流逝性、暂时性;同时性意味着诸显象在瞬间共在的状态。换句话说,审美关注是一种对事物在“此地”与“此时”的“出场方式”[51]的关注。“此地”是当下的空间维度,“此时”则是当下的时间维度,但核心还是“此时”,因为在“此时”的主体必定在“此地”。“出场方式”是在弗雷格对“含义”与“指称”[52]做出区分时所用的概念:“晨星”与“暮星”二词含义不同(出场方式不同),但指称的都是同一颗星。因此,在逻辑性的语言运用中,事物的出场方式并不重要,但审美则相反,出场方式是第一位的,事实性反而是第二位的,这是一个关键。
这就成全了显现美学的一个核心成果:彰显了审美活动的随时随地性。审美感知并不是对固定对象的感知,而是对任意对象身上出现的显象游戏的关注;审美不是一种独特的经验领域,而是人类经验的一种独特可能性,它针对的不是独特对象,而是我们遭遇对象的独特方式。这个观点听起来像传统的“审美态度”理论,但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区别,传统的态度理论并未能避免陷入主观主义、幻觉主义的危险。而在这里,这种随时随地性并非一种任意性,而是一种“遭遇”。“遭遇”意味着,事情的发生既不完全取决于主体意志,也不完全取决于所谓客观现实,而是一种“发生”。这种遭遇原则上不可重复,但它也并不神秘,不那么偶然。它的基础,亦即“显象间的游戏”本身并不是主观任意的。任何人都能观察到草地上各种显象在每一瞬间不同的显现,即使没人路过,显现也在发生。显现虽然不能脱离人类经验的可能性,但可以脱离某一个人的具体经验。这就是显现的客观性。这也是现代哲学对客观性的拓展,即不再是洛克假想中那种“物质”的客观性,而是“主体间”可确认的客观性。[53]
专注于“出场方式”的审美感知是对“此地”与“此时”的“当下”的感知,是对“同时”与“瞬时”的显象之充盈的逗留,是对“显象间游戏”的关注,从而也就是对“显现”的关注。
因此,“显现”概念为当代美学赢得了一个更具有包容性,也更立场清晰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