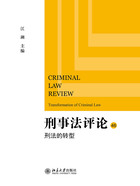
二、俄罗斯刑法的去苏维埃化
苏俄刑法是社会主义法系国家刑法典的典型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社会主义法是一种新型的法,因此经常被视为一种与资本主义法性质不同的法。”1在苏维埃法学家看来,社会主义的法,从其建立之初,便与资本主义的法相区别。苏维埃初期,曾任司法人民委员的斯图奇卡便认为:“对于旧的法典,必须彻底地、毫无保留地加以摧毁,我们要运用新法院和现实生活每天提供的那些创制法律的材料。”2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建立的苏维埃刑法,在经历了苏维埃末期和社会重建后,受到了强烈冲击。 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更是从刑法的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和具体刑法制度上,与苏维埃时期的刑法相区别。3苏联解体后,新生的俄罗斯社会,对苏维埃时期的刑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沿着去苏维埃化的道路,改造和发展了当今的俄罗斯刑法。
(一)去意识形态化
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动摇是从思想上导致苏联社会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整个苏联社会面临着思想领域的重建。苏维埃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建立的刑事法律制度,也面临着俄罗斯学者的重新审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首要任务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清理,以便在新思想的指导下建设一个新的俄罗斯国家。然而,意识形态与法律存在天然的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已。法律的这一属性,并不会因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的起草及其颁布后的修改过程,始终伴随着刑法的去苏维埃化。在俄罗斯刑法去苏维埃化过程中,众多学者将意识形态化与苏维埃化紧密相连,似乎意识形态化成为苏维埃刑法的代名词,似乎只有苏维埃刑法才是意识形态化的。当然,后苏维埃时代俄罗斯刑法的重建,是与整个俄罗斯社会的重建过程相吻合的,是作为俄罗斯社会重建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这就必然要求俄罗斯从立法的指导思想、理念、价值、目的、任务等根本性问题,重新审视苏维埃时代的刑事法律制度,必须让后苏维埃时代的刑法适应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生活,以刑法来保障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成果。 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是俄罗斯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学界对犯罪的概念、社会危害性理论等刑法理论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激烈论争。在强烈的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之下,俄罗斯学界似乎认为可以创制一部非意识形态化的刑法典。
在经过了苏联解体带来的社会阵痛后,俄罗斯学者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强烈的刑法去意识形态化问题进行了反思。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罗斯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的鼓动下,将国家意识形态仅仅看作消极的现象……有观点认为,意识形态与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现象。法律应该独立于意识形态,或者说,在意识形态范围内,法律的作用就弱化了,进而与人与公民的利益不符。”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1993年《俄罗斯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这是贯彻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前提。然而,这却忽视了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按照法律与意识形态相分离的论点,似乎,与自然科学一样,法律也可以做到非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表征国家意志的刑法,难道真的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吗?
社会科学不仅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还需要对“应当是什么”作出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民族,都会有不同的回答。在价值领域,民族性和国际性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关系将无法消除。甚至不存在脱离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的社会科学。美国学者奥威尔认为,如果将政治一词作最宽泛的广义理解的话,“没有一本书是能够做到真正脱离政治倾向的”5。曾经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阿塞拜疆学者拉基莫夫也坦言:“犯罪的概念与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有关,与何为有罪并应当予以刑事处罚、何为无罪且不予处罚的观念有关。” “将一些行为归入刑事犯罪,而其他行为归入行政违法或民事行为的真正根据,只有在相应民族历史进程的土壤中才有可能找得到。”6因此,无论是哪一国家的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走一条非意识形态化的发展道路。即便是学者存在刑法非意识形态化的意愿,最终也不会改变刑法所带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刑法去意识形态化的论点,本身就不能够成立。在意识形态的长期滋润中,官方主导的思想体系已如春风化雨般内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已经自然而然地遵从意识形态的指导,不知不觉地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选择、控制和实施自己的行为。同样,意识形态通过法律的目的、任务、原则等,对法律规范具体制度的建构发生作用。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构建出了不同价值取向的法律规范,又进一步地作用于人的行为。意识形态、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在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指引下,立法者所设立的刑事法律制度,具体地履行着保护与保障并重的价值追求。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是不可能非意识形态化的。仅仅可能的是,从一种意识形态为主导,变成另一种意识形态为主导。
(二)重新审视俄罗斯刑法的基础理论
在推进俄罗斯刑法去苏维埃化时,自然需要对苏维埃时期形成的刑法理论进行反思。在部分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刑法苏维埃化的典型代表,进而,主张废弃实质的犯罪概念和混合的犯罪概念,回归1903年《沙俄刑法典》规定的形式的犯罪概念。“在国内刑法理论中,对犯罪概念的立法表述进行过激烈争论:它(犯罪概念——引者注)是否应包含实质特征,或者仅限于形式特征,还是兼而有之。”7在这一论辩过程中,曾经有一种非常普遍的观点认为,实质的犯罪概念就是苏维埃刑法的一个特征,体现的是一种镇压关系。形式的犯罪概念,和资本主义时期倡导的民主、自由理念相符合。为此,要突出刑事违法性特征,以彰显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意义。在强调全人类价值优先,强调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规则与准则优先的情况下,主张废除带有某种阶级意味的社会危害性概念。然而,这种将社会危害性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化、等同于苏维埃刑法的看法,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得到了纠正。多数学者认为,作为犯罪实质特征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是国家镇压功能的助推器,国家的镇压功能,也并不因犯罪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的存废而发生改变。相反,社会危害性特征,恰恰是犯罪的本质属性。俄罗斯学界在对作为俄罗斯刑法根基的社会危害性理论的长时间争论后,还是保留了其传统的刑法理论。8无论是社会危害性理论,还是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都是当今俄罗斯刑法学界的通说。社会危害性得以保留于现行《俄罗斯刑法典》,并作为一项重要的理论根据成为俄罗斯刑法上诸如犯罪概念、犯罪分类、刑罚裁量等重要制度的基石。尽管如此,俄罗斯刑法理论界对被认为是苏维埃刑法制度代表的社会危害性的质疑却并未停息。在意识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俄罗斯,却并未撼动苏维埃时期形成的刑法理论。无论是犯罪的概念、社会危害性理论、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等,都保持了苏维埃时期的基本面貌。当代俄罗斯学者所努力做的,便是在意识形态发生剧烈变革的情况下,对原有理论的改造与发展,使之适应俄罗斯社会的新形势。
(三)强化对各类财产的平等保护
俄罗斯刑法去苏维埃化,还体现在其刑法分则的变化上。戈利克教授明确指出,刑事法律禁止的意识形态内容体现在“刑法典分则相应条文的罪状中和刑罚上” 。9在俄罗斯刑法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对不同财产的保护力度便反映了这种巨大变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出现了私法的复兴。这种私法复兴的理念,在俄罗斯的民事和刑事法律上均得以贯彻。私法复兴,实际上复兴的是人人平等以及在人人平等基础之上对个人意思自治的充分尊重与保障。作为个人追求幸福物质基础的私有财产,必然成为刑法关注的重点。俄罗斯刑法典把私有财产的保护列为优先任务,并在刑法总则与分则的相关制度上予以贯彻。按照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私有财产神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个体权利和自由并列的价值要素。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是自由主义者无法回避的中心议题之一。“按照所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承诺个人自由即蕴含着对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规则的赞同。”10在财产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实现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
在苏维埃时期,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刑法,必然要对公有财产进行特别保护。这在刑法上的体现便是对公有财产的保护力度明显大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盗窃公共财产的规定便是如此。在苏维埃时期,对盗窃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刑事责任要远超过盗窃个人财产的刑事责任。例如,按照1926年《苏俄刑法典》第162条的规定,盗窃个人财产而判处的刑罚要远比盗窃公共财产的刑罚低。根据该条的规定,窃取一般的私人财物,判处的刑罚仅为3个月以下的剥夺自由,而从国家仓库、公共仓库等处窃取财物,则要判处2年以下的剥夺自由。11根据财产属性实现对不同财产形式的不同保护,曾经是苏维埃时期的常用方法,以突出刑法对公有财产的重点保护。在苏维埃时期,公有财产处于优先的保护地位,而在解体后的俄罗斯,私有财产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俄罗斯刑法分则去苏维埃化的典型表现就是加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实现公有财产和公民个人财产的平等保护,尤其是优先保护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是俄罗斯刑法改革过程中去苏维埃化的重要体现。在从苏维埃刑法向现行俄罗斯刑法过渡的过程中,在认识到公私财产的平等性后,俄罗斯从立法上取消了因财产属性而给予不同刑法保护的规定。
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规定了没收财产刑。部分俄罗斯学者认为,一般没收就其本质而言,违反了俄罗斯宪法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 2003年修改俄罗斯刑法的联邦法律用罚金代替了没收财产刑。进而,将这一可能对公民合法财产进行没收的制度废除掉了。没收财产刑被废除后,俄罗斯学界出现了众多的批评之声,认为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腐败犯罪的情况下,废除没收财产刑是不适宜的。在此情况下,2006年俄罗斯又以联邦法律的形式将没收财产纳入其刑法典,但此时的没收财产已经变成了特别没收,仅能对那些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进行没收。这种特别没收被规定在了《俄罗斯刑法典》“其他刑事法律性质的措施”一章,严格而言,已经不再是刑罚的种类,而是类似于保安处分的一种犯罪预防措施。并且,为了限制特别没收的适用,《俄罗斯刑法典》规定了严格的可以适用特别没收的犯罪清单。12俄罗斯社会对没收财产刑的重新定位,实际上表明俄罗斯国家政治对刑事立法的影响。作为国家基本法律制度的刑法,在全俄境内具有统一适用的效力。但是,俄罗斯刑法到底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判处何种刑罚?这样的问题,却是需要经过立法程序进行确定的。在俄罗斯,总统、俄罗斯政府、国家杜马议员、最高法院、俄罗斯宪法法院等机构,具有向国家提出刑法修改的建议权。这样,刑法实际上是政治的延伸。一般没收财产刑的合理性,也是我国当前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针对我国刑法上的一般没收问题,我国学界基本形成了“没收财产刑是缺乏正当性的,应当予以废除”13的共识。
比较中俄刑法可以发现,俄罗斯刑法上没有贪污罪这个罪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贪污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国家财物的行为。贪污罪中的窃取与盗窃、骗取与诈骗有何实质区别呢?区别在于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身份不同和利用了职务便利。如果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或骗取了国家财产便构成贪污,否则便构成职务侵占、盗窃或诈骗。如果仅从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上来理解贪污罪,那么,在平等原则之下,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要求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要求应该并无不同。如果说有不同的话,不同之处也就在于侵吞、窃取、骗取财物的性质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大力减少因财产属性不同而进行的差异化定罪。也正是因此,在俄罗斯刑法规定的腐败犯罪中,没有规定贪污罪。那么,俄罗斯对于发生的类似于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行为”,是如何进行认定的呢?实际上,利用侵吞、窃取和骗取手段实施的“贪污行为”,其本质就是一种职务侵占、盗窃或诈骗。这种行为被《俄罗斯刑法典》第159条诈骗罪和第160条侵吞或盗用罪所规制。只不过,具有职务身份的人,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在商业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上述行为的,是该罪的加重情节。因此,俄罗斯刑法在惩治腐败犯罪方面,淡化了刑法的身份性,强调对各种类型财产的平等保护。这样俄罗斯刑法便排除了基于财产性质而影响定罪的因素。当然,俄罗斯刑法的类似改变,是与俄罗斯国家性质发生的变化存在密切联系的。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宪法,强调各类财产的平等性,进而不再根据财产的不同属性在刑法上进行差别保护。
当然,俄罗斯刑法的去苏维埃化,绝不仅仅体现在上述几方面,而是涉及整个俄罗斯刑法体系的构架,涉及刑法的目的、任务,刑法的指导思想。这些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俄罗斯刑法的自由化和人道化有关。
在中俄刑法学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刑法的“去苏俄化”和“去苏维埃化”的主张。但是,将两个术语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极大的差异。相同之处在于,中俄两国学者都努力去除本国刑法上的苏维埃时代的烙印。但是,我国部分学者主张的刑法知识“去苏俄化”与俄罗斯刑法学界提出的刑法“去苏维埃化”却并不相同。我国学界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论者及其拥护者,看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苏俄引进的刑法理论知识,试图从刑法理论层面挣脱苏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的桎梏,实现中国刑法理论的革新抑或转型。这种“去苏俄化”的主张,实际上并未触及我国刑法的目的、价值等根本性问题。与中国的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努力方向不同,俄罗斯刑法学界的“去苏维埃化”,却是对原有的苏俄刑法传统的一次彻底改造,甚至是对传统苏俄刑事立法的一次重建。中国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主张,实际上已经是对中国刑法发展道路选择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刑法未来的发展之路。
1 〔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2 〔苏〕皮昂特科夫斯基主编:《苏联刑法科学史》,曹子丹等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3 See Ekaterina Mishina The Re-birth of Soviet Criminal Law in Post-Soviet Russia Russian Law Journal 2017 1. pp. 57-78.
4 Радько Т.Н. Об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функции права// Вестник Саратов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юридическойакадемии. 2013.№ 4. C. 73.
5 George Orwell, Why I Write, in The Orwell Reader, 1956, p. 394, 转引自〔美〕耶鲁·卡米萨:《法学教授为什么应当学术写作?》,刘磊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年第1期。
6 〔阿塞拜疆〕拉基莫夫:《犯罪与刑罚哲学》,王志华、丛凤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7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уголовного права. Т. 3. Поняти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Издание профессора Малинина. СПб. 2005. С. 48.
8 参见龙长海:《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原社会主义法系国家的当代命运》,载张仁善主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205页。
9 Голик Ю.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дея 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ее отражения в уголовном законе и в уголовномправе.–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Асланова Юрид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есс 2007. С. 57.
10 〔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11 参见《苏俄刑法典》,郑华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70—71页。
12 参见龙长海:《一般没收财产刑:俄罗斯经验与中国现实》,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13 时延安:《论没收财产刑的废除》,载《南都学坛》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