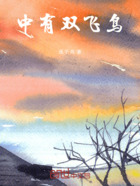
第2章 难题
庐州卢氏属范阳卢氏大房的一支,卢照今是卢氏独女,家中还有个年长五岁的兄长,卢升曾有个早产的次子,过继给了宗中大房抚养,后来生的卢照今,也是个体弱多病的,终是不好再过继。
幸得幼时一道士点化,卢照今跟着修身养性多年,身体不再孱弱,十一二岁归家,却养成了这跳脱的性子,不存敬畏,挨了不少训诫。但离家多年,缺少关爱,卢氏一家对卢照今的宠溺多过责罚,又是个女儿,便由着她的性子闹腾,只有卢升常板着个脸作严父姿态,能让她忌惮几分。
卢升觉得她顽劣,便给她取了个严肃的闺名。“其身正,不令而行。”唤作令儿,希望她能时刻约束自己。对她的教育也与寻常女子不同,多教学诗文经典,常亲自督促教习文学功课,比男儿不妨多让。文化繁荣的背景下,贵族女子多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但同男子般严厉的并不多见。
直到他人向卢升引见了高齐物。沈国公府子孙,孤身只影,年方十九,一表人才,又勤奋好学,颇有才气。卢照今正是少女豆蔻年华,天生丽质,身如蒲柳,性格虽有些叛逆,教养却无所欠缺。卢升有意招高齐物为婿,亦当养子看待,给予不少帮助。
待高齐物成了乡贡,便向州道递了婚书,成了婚礼,太过自然,倒显得有些突兀。
高齐物常觉得自己是见色起意,一见卢照今美貌就失了分寸,草草把人生大事定下了。卢照今的一颦一笑,牵动着高齐物的心绪,笑靥明媚似三冬暖阳,颦频蹙促似湖面清波,时常梦中醒来嘴角犹带着笑意,让卢照今认为他犯了癔症。
卢照今知道他是个喜欢胡思乱想的,却在行为上极有分寸,与自己性格上一谨一随,两人互补,相处融洽,他人眼中卢照今性格骄横恐非良配,高齐物却不以为意。高齐物行事郑重,思想有时却比卢照今还跳脱,令卢照今觉着颇为轻松,两人情投意合,感情日渐深厚。
高家住宅是个三进的大院落,算是高继留下的遗产里最值钱的部分。高继在庐州深受百姓爱戴,欲在庐阳建屋的消息传出去,百姓自发捐赠砖瓦木材,选址开拔后不少人来帮忙,最终建成了这顶格的三进大屋。但高继在城中有自己的官舍,并不常住这院落。高继迁官后官舍收回,家眷也就都搬回了县里。斯人已逝,只有这宅子不见什么变化。
下人王晁清早出门,不到两刻钟就将马车借了回来,高齐物出门时,正好看见王晁将马车往后门赶,高家没有马厩,只有用作堆叠杂物的后罩房,院中可以停马。十六辐的车轮,显然是从哪个士绅家中租借的。
“郎君。”
王晁勒停马匹,冲高齐物行了个叉手礼,高齐物颔首回应,只见高齐物系着披风,拎着个包裹,似是要出门。
“郎君可是要出门,我送郎君?”
高齐物见他身着纸衣,牵马的手冻得青绿,也不打算再让他受累。
“归还一些书籍,不远,用不着坐车。”
“郎君歇着便是,这种跑腿的事仆来就是。”
“我亦会挑选借阅一些文书,你可帮不到我。”
摆了摆手,作势欲走,又回头提点了几句。
“厨房熬了姜汤,你也喝碗去去寒,支取些布匹做件新衣裳,你这寒衣都硬了。”
“其他的事等我归来再报,天寒地冻,无事别冻伤了身体。”
登时王晁寒意已经去了几分,高齐物不在府学致学,地方上的先生他看不上,身边不需要也就没有书童,只身就向衙门走去。
“劳烦少吏通告一声县尊,高氏前来拜谒。”
门口小吏认得高齐物,也不过问,向内传告,不多时便有个下人出来,引高齐物入后邸。前衙是长官行使权力的治事之地,包括大堂和二堂;后邸则是县官办公起居及家人居住之处。
县令不同于县尉与县丞,后两者多有调动,县令却是有固定任期的,边远地区的县令任期可能只有三年,而内地县城县令任期满五年才可升迁,肥西属于紧县,县令要五年才期满。县令韦元甫出自京兆韦氏,举进士铨选成了肥西县令,并不依靠韦氏的门荫。
“明府。”
高齐物入中虚身一礼。韦元甫正坐案前,手中看着州道传达的公文,见高齐物前来,微微颔首,随手指了张椅子,示意高齐物落座。
“不用拘束。”
高齐物有个任州道长史的岳父,又有个声名远播的刺史老师,本身还是申城公府子孙,韦元甫对他可以说相当客气。
“可是来还公文邸报?”
“如明府所言来归还公文邸报,亦来借阅一些时策文书。”
科举有许多科目,明法、明经等科只需要熟读法律经典,进士类的科目就需要考察策论问答能力了,多与时策相关。高齐物不在府学,没有试卷考察先生解惑,只能自己通过时策钻研。
“不急,我已备好了,过后让下人去取便是。”
“多有叨扰。”
“无妨,家师与卢长史为同期,你我还是同辈。”
“何况高郎君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八岁便能作文行章,十岁便一人主持家务,十二才动淮南,引得欧阳公收为弟子,为我庐州人杰,我助力是应该的。”
“明府过誉。”
“不必太过自谦,青年才俊当有自傲之心。”
“素闻高郎君才高,有‘绯鹄’之名,某恰有一难题,高郎君可为我解忧?”
(鹄袍是旧时应试士子所穿的白袍,绯色是五品以上高官才能穿的服色,绯鹄指高齐物金榜提名是板上钉钉的事)
高齐物一愣,相交韦县令只是淡漠,与自己关系并不亲近,这般态度直白,恐怕这难题正是难在迫切,旋即目露恭谨之色。韦元甫似看出他的想法,轻笑缓解气氛。
“不是甚大事,只不过为族中事物所困,烦恼罢了;还劳烦高郎君献计。”
人生在世最怕欠人情世故,韦元甫上来就摆出了卖人情的态度,可见他是真拿不出主意。
“不知是何事,令明府如此烦恼,失了分寸?”
“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先听一听再做打算也不迟,害不到高兄。”
“称不上明府一句高兄。”
高齐物依旧矜持,年龄上韦元甫比高齐物大了十几岁,称兄道弟有点勉强,地位上高齐物只是乡贡,比韦元甫还低一等,一方县令这般放低姿态,必不是什么小事。为了一个县令的人情摊上什么大事可不值当,可又不好落了县令的面子,只正襟危坐,并不言语。
韦元甫也不管高齐物态度,自顾自开始讲述。
“我自彭城公房出人,我彭城公房人口众多,产业庞大,多为土地经营商业贸易,个中关系并不复杂,族中常有龃龉,但也算一团和气。”
“今我族中有一友,为族中丝绢采购之职,为人仁孝忠义,每年为族中节省大笔出项,宗主对其颇为器重。”
听到丝绢,高齐物本能的感到所闻事况干系不小。
租庸调法,作为开国就开始施行的税收体制,租庸调法的实施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的。均田制是由朝廷将大量无主的土地收归国有,再按人口数分给百姓耕作,初期均田制就规定成年男子每人可“授田百亩”,这一百亩田地又被划分为二十亩永业田和八十亩口分田。
永业田的二十亩土地是归百姓私有的,可以世代传递,也可以在百姓迁徙或者因家贫需要安葬费时出售,但一经卖出,朝廷就不再次授永业田。而八十亩口分田则归国家所有,只是暂时交给百姓使用,耕种者去世时则由朝廷收回(百姓迁往人少地多的地区时也准许出售),再根据情况重新分配。
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政府就可以按照授田记录向百姓征税。百姓不论贫富,一律缴纳定额的租庸调,初时这一税制被称为租庸调法,其中租指田租,每年纳粟二石;庸指劳役,每年替朝廷服劳役二十日;调是户调,即按户征收一定数量的如麻布、丝、绢等农产品,其中丝绢为户调主要收取对象。
租庸调法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允许百姓交纳丝绢以代替劳役,在国家需要百姓服役的时候,如果加役超过十五天,则免其调,加役超过三十天,则同时免除租和调;再比如在出现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则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则全免。
建立在均田制上的租庸调法使得百姓既有土地耕种,又不会因为长期服役而耽误农时,更有面对灾情时的减税方案。
初时,朝廷通过这一政策安置了大量流亡的百姓。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租庸调法的问题也渐渐显现出来。
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指最初给百姓授田的地方,如果此人迁居别地,则登记为客户,按律法规定,主户需要缴纳租庸调,而客户则不需要缴纳,于是许多人将手里的土地卖掉,移居别地、不再缴税;而购买土地的人则想方设法将土地隐藏起来,不在地方登记,也就是所谓的逃户,这就造成了税收的大量流失。
其次,一部分被授予土地的家庭,在应该归还口分田时不愿意上缴土地,而是隐瞒实际情况,导致朝廷掌握的土地数据严重失真,影响税收。
由于均田制分配的是无主土地,地主阶级的土地仍归私人所有,因而贵族阶层便常常借助家族势力和官僚权力扩大自己的土地。
高继便是因对逃户的纵容,最后被迁往岭南,落了个病死道中的下场。
像韦氏这样的大族,隐田、隐户不计其数,所需的丝绢亦难以估量。事主为一房采购户调所需,地位不会低。
“这丝绢涉利之巨,想必高兄也了解。我这亲友虽正直,亦受族人裹挟不能免俗,以致到了骇人的地步。虽不曾主动贪墨,对恶行未加制止却是实打实的。”
“如今事态初显,其悔悟愧对宗族,亦不忍亲友在歧途走至末路,可一边是族中亲友,一边是宗族利益,我这朋友身陷其中,我实在不忍他日日受此煎熬,我知高郎君才智超绝,望求良策,以全其忠孝仁义。”
高齐物一惊,暗骂这韦县令鲁莽无赖,这种事一入耳想必是无法脱身了,先前的安抚现在看来分明是敲打。
采购之职,涉议价、运输、储存、流通等诸多事宜,保不齐参与些隐晦事,回扣、做虚、压款更是司空见惯,想把采购一职做好,就没有干净的,自己不贪,却可让给他人做人情。家族生意亲友中饱私囊,自己也身涉其中,如今事情有败露的迹象,想要脱身。
现下事主事已危机,眼看年关到了,也到了清账的时候,各方瞒的再好,也终有败露的时候,索性现在就解决,好过终日忧虑。若不理睬,积弊成疴,迟早把自己冲个头破血流。可宗族生意,一旦检举便是和族亲结下恩怨,利益事小,事涉人品,必将极大损害自身的声名。
高齐物低头沉思,韦元甫做法着实大胆,把这腌臜事将外人参谋,还求助到一个并不相熟的身上,可见韦元甫真是被逼急了,想来这事也有他一份。万一自己拿不出主意今日事又该如何收场?
不,不如说内部的尖锐问题让外人出谋划策才妥当,越与之不相干越不可能泄密,外人也没法接近韦氏高层,才能在彻底败露前寻一个回旋的余地,谋一个万全之策。
高齐物心中对韦元甫的想法赞叹,看似鲁莽,实为胆大心细,一方县令确实有其智慧。认可韦元甫能力的同时,问题也已经有了对策。
“明府既如此信任我,那我必竭诚谋划。”
韦元甫难掩喜色,他有赌的成分,这种辛秘事同一个陌生的外人交底,需要莫大的勇气,所幸他赌对了,高齐物是个聪明人,也是个聪明人。
“幸得高兄相助,我代我这朋友先谢过高兄。”
高齐物抬手虚礼,靠在椅背上,开始组织语言。
“明府可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韦元甫不明白高齐物话里是否有什么深意,只微微颔首。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一为慈一为孝,二者皆是美德,当慈孝与大义相悖,孰对孰错,孰是孰非?”
“敢问明府,今子为堂官,若父被追罪,子当如何。”
“大义灭亲?”
“有失人伦。”
“徇私包庇?”
“行事不端。”
“如之奈何?”
“若我为堂官,当弃官而去庇父逃亡。”
韦元甫与高齐物相视一笑,一捧一逗,气氛轻松了不少。
同样的行为,不同的立场决定了态度。兄弟劝你忠义,那就是让你选义,朝廷要求你忠义,那就是让你选忠。
“隐而不发只会在决堤时让洪水更加汹涌,贸然告破恐怕众怒难消;有些事并非不做,而是需要恰当的方式。”
“说到底,所求的不过是一个两不得罪,夹缝中脱身。可使事主生事,事不必太多太大,因果却要繁杂,动静闹大,引着他人去查,牵出背后诸多关系,到时众人自然无暇他顾。”
“待到事缓,上位者必能意会个中深意,处理也会看着情分照拂多方脸面,终得圆满。如此既解眼下之困,又不失仁德,昭其忠义。”
韦元甫一听,神色舒缓,暗叹高齐物急才,想法不拘一格,又觉得高齐物作风过于老成,全无青年风茂。弃卒保车,抽身泥潭,不毁声名,举报后只管调查自己,背后查出来什么那就不关自己的事了,面子和里子都保住了。
高齐物敢用计如此大胆还有一个原因,事主深得家主器重,又是家族内部事务,必然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
“得高兄智计,解我忧愁。”
再一细思,韦元甫面露喜色,便向高齐物致谢。
“高兄勉力相助,我却无以为报,听闻高兄不日将入府学,州学中有一正堂,是我同窗好友,可为高兄答疑解惑。”
高齐物来年三月就要赶赴春闱,卢升将他安排进了府学,巩固练习,现在韦元甫又帮他找了个教授来辅导功课,对人称“绯鹄”的高齐物而言这辅助过于充裕了。
“韦某受助,不敢相忘,只是事务繁忙,不能尽谢。”
高齐物看着韦元甫,面色古怪,这韦元甫当真是个没脸没皮的,拉的下脸面。好在今日事妥善解决,不然少不了这韦县令一顿拉拢敲打,当下一心遁走。
高齐物也不多嘴,只回了个礼,韦元甫想留人,却也看出了他的意思,唤来奴婢,为高齐物取了许多时策文书,还欲赠予钱财,被高齐物拒绝了。
出衙门时,还不到巳时,莫名就参与了一件大事当中让高齐物有点恍惚,高齐物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又说不上来,索性不去想,时间还算充裕,高齐物也起了逛街散心的兴致。
“十五郎可满意?”
韦元甫身侧的案旁坐着一个青年,身着澜袍,束发及髻,清朗俊逸,正尝着杯中茶水,闻言也不抬头,将口中并不算差的茶水吐尽,一副嫌厌之态。
“一般。”
韦元甫面露尴尬之色,这韦十五郎当着自己的面吐出了茶水,作此敷衍回复,自己算起来还是长辈,完全不给面子。韦元甫只能宽慰自己这韦十五郎高傲惯了,也不善与人打交道,况且自己只是个进士庶子,说不准这进士还受了韦氏恩泽,这韦十五郎却是房公嫡子,权当没看见。
韦十五郎以为韦元甫没听出自己的深意,又加上一句。
“你出的主意也是。”
韦元甫面色微愠,这韦十五郎是真把自己当傻子了。
“我既向你们问计,自是为好向阿爷交代,又不伤族亲和气,你们也能有个好下场,如他说的般自投罗网,岂不让他人耻笑。”
韦明哲,韦氏宗主韦元昭嫡三子,韦十五郎,世家贵子,自然不屑于行腌臜之举,可终归是一家人,对以权谋私的行径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料前日查账输税,库房丝绢竟不足数。
韦明哲不怎么通晓人情世故,更何况是家族产业,错综复杂,拔出萝卜带出泥,他没有父兄那般坚定果决,也不同于他们手握权力,不好得罪这帮族亲,一直拖到现在。
明面上有一粒坏米,暗地里怕是到处都是。韦明哲这才敲打韦元甫等人,这些旁支庶出,在族中既无甚话语权,又无要紧官职,出了事第一个拿他们开刀,最应该急的就是他们,韦元甫正是其中代表。韦元甫也是焦头烂额,怕等到一缸米坏透了,事情可就没法挽回了。
韦元甫一个头两个大,困扰这么久的问题,如今终于有了对策,这韦十五郎又出幺蛾子了,几欲怒骂,但想着自己命脉把握在他手里,还是忍住了。
韦十五郎自诩世家贵胄,又是嫡子,自然看不起韦元甫。韦元甫虽然是庶子,但也是韦氏子孙,与一群贱民同争进士,他觉得膈应。他是个爱干净的,这等被钱财侵蚀的人,他不想有太多接触。
韦元甫自己也身涉事中,甚至以自己县令的权力包庇隐田,收受好处,同高齐物说的事主,既是韦十五郎,也是他自己。况且韦元甫未出户,事事都得看嫡系脸色,哪敢出言不逊。心急如焚,面上却不好表露,
“十五郎此言差矣,岂不闻大智若愚,大巧如拙,这对策虽看着愚蠢,实际上却精妙,宗主等长辈皆人中龙凤,这等计策反而不会被识破。到时宗主看出其中深意,也会认为十五郎聪慧。”
韦十五郎也是个聪敏又心善的,心知韦元甫等人在族中无甚话语权,才同他们通气,自然明白其中妙处,此刻正是不喜韦元甫市侩,故意刁难,反被韦元甫看轻了,也有些恼了,暗地里咒骂,嘴上应和。
“阿爷的才智,确实需这等大智若愚之计才能应对。”
韦元甫满心欢喜哄好了这尊大佛,嫡子都以这样的方式自白,一经查处,就怪罪不到自己这样的小人物,却不知自己已经被韦十五郎记恨。
韦十五郎解决了一桩心事,心情也舒畅,他经办丝绢采购,自苏州赶回长安,途经庐州,想不到韦元甫真有谋身之计,其人却是个贪婪庸碌的,戚戚做派,全无县尊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