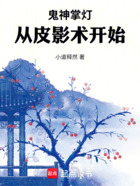
第8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柳苗算了算时间,她知道今天正午就瞒不住了。
纸包不住火。
她这几天,在城里打听消息,串起来也猜出几分。
“几家人都去了季县,老舅就是再傻,也该知道出事了。”
“只是季县舅家,家庭贫寒,牛车,总归比不上快马,要来,也会晚一些。”
她还得等一等。
....
....
“若是刘夫子故意这么做,看似公平,事实上把几家都得罪了。往后谁家都不敢保证被来这么一次,别说传诵他那些经典了,就是咱们环县这几家,怕是都要人心各异,以后要做点什么,都得仔细盘算盘算。”
柳家二郎毕竟是未来要接任家主的人,到底清醒的多,分析的头头是道。
柳老太爷拉拢着眼皮,仿佛睡着了一样。
时到今日,所有人自然确定了柳柳州拿了那件东西。
柳家二郎又细细分析了一下,是说给堂下坐着的小儿子听的。
柳二郎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常年都在外面学习,只有柳祖计培养在家,虽说养在大房,显然重点培养。
柳祖计听的仔细:
只是放出这么一个消息,其中居然这么多门道。
到头来,自己崇拜、信任的夫子,居然是操控的人物。
“就是不知道柳州是怎么搭上夫子这条线的,到头来,所有人都把筷子放进去了,才知道是咱们家的锅。”柳二郎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柳老太爷似乎对这一句比较满意,敲了敲桌面:
“一家人吃饭,积极的吃的多,不积极的,碗都端不住,怪谁呢?”
殷氏尴尬的赔笑:
“孩子没吃好,做父母的责无旁贷,可能是月初,大哥那一巴掌,打的他心里有气。”
“不止那一巴掌吧?”柳老太爷说道。
殷氏沉默了片刻,回答: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当初说好一家借百金给那孩子看病,最后慢慢再还,没想到大哥反悔了,柳青那孩子脾气倔,才动了手。”
“我怎么听说,有人想要那孩子小举选拔的名额?”
柳老太爷的声音不大,却在堂中炸响。
柳家二郎柳瑞丰震惊的看向殷氏,他常年在外,领着皮影班子,家里由老大做主,议事也是有殷氏参加,没想到发生这种事。
砰!的一声,柳二郎一拳锤在身前的桌面,茶水四溢。
“老三家里才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传出去,叫我怎么做人?”
柳祖计也没想到其中还有这么多隐情,此刻他想到了那日见柳苗的场景,顿时明了,生出愧意。
殷氏始终平静的坐着,似乎与她无关,她只是一个称述者。
片刻后,气都消得差不多了,柳老太爷又敲了敲桌面。
“事情都知道了,该过活,还得过活。”
柳二郎也冷静了许多,重新开口:“爹,既然大哥说那东西不在季县,这么短时间,会去哪里呢?该不会,始终没出县城吧?”
殷氏心中有些无奈,扯了扯丈夫的袖子。
柳二郎此时心中有气,埋怨殷氏没告诉他实情,不想搭理。
却见殷氏搭上他的手肘,伸出三个手指。
他想甩开,看到妻子奇怪的举动,心中一愣,假意捋了捋袖子:
“对啊,肯定在那里,要炼这东西,就得去火窑,老三和三叔有过来往,说不定有交情。爹,我现在就备车,去东城火窑?”
柳老太爷却不紧不慢:
“吴、侯两家,跟着你大哥扑了个空,人家会想不到?”话锋一转,又说道:“老三是和我不对付,不过想从他手里抢到东西,可没那么容易,不然,当年也不会十几岁就离家出走,一走就是三十年,你爷爷到死不肯原谅我。”
柳二郎震惊的看着老父亲,传言当年,柳家老太爷夺了柳老三的功名,还占了本该过门的媳妇,以至于柳老三离家出走,三十年未归,老老太爷死不瞑目。
“爹,当年的事是真的?”
柳老太爷猛的睁开眼,眼中阴鸷逼人,似乎这是不容任何人触碰的逆鳞。
“刘俞舟除非不想做这个教谕,以后只想安心当个教书匠,他以后的路能走下去?!”
不像是质问,到更像是下决定。
“孩子大了,知道分桌去吃饭,就是不知道,他是上的饭桌,还是砧板。
备车,去学塾。”
话刚说完,门外就来了个衙门传话的。
“请柳家家主前去一叙,还有吴家、侯家也去请了,车在门外候着。”
柳老太爷阴晴不定的脸上,片刻,由阴转晴。
难得流出些许笑容,心平气和的回了一句:
“刘夫子,定然儒学深厚。”
....
....
下人陪着柳老太爷出去了,留下柳二郎一家三口。
柳二郎疑惑:“爹刚刚还不高兴,怎么听到,刘夫子请,就转了脾气。”
殷氏笑了笑,似乎先前的指责并无多大影响。
看了看旁边的儿子柳祖计,轻声说道:
“你爷爷不去火窑,是因为三爷爷在那里,就算是县里有人去,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问题。反而是,该做主的是刘夫子,这东西是他的,他要是等咱们自己找上门,显然是想撒手不管,想必以后,儒学就没人支持了,起码明面上是这样。
刘夫子能派人来,说明他要解决这事。来的是县衙的,说明身份不一般,又点名要家主去,自然是奔着解决事情的。”
柳祖计听了,发出疑问:
“夫子为什么这么做呢?”
...
...
几家家主进的是县衙,几人被安排在一个房间,见了一个年轻人。
原来刘夫子几天前就进京了,京都大儒过八十大寿,点名要这个学生回去。
来通知的人,顶替的职务,处理剩下的事。
几位老家主,看了一封信,一人拿了一样东西,几人满意极了。
环县的县令居然沦落到没有资格进去听说的地步。
只是冯县令到是极为识时务,对此一点不恼怒。
书房里与师爷喝着茶:
“此次刘夫子回去给老师祝寿,看来,来年要留在京都了。”
师爷点点头:“我见那位大人,给了三家,一家一件入品的物件;要不说读书人就是体面,看来开春小举,不光儒学政绩光彩,发扬光大,老爷也得一份褒奖。”
冯县令一阵肉疼,又有羡慕,又嫉妒:“上面人动动手,指甲缝流出来的,整个环县都能吃饱。”
转念一想,又问道:“不是桌上还剩下一道菜吗?你带人去找回来,我不信还能长腿跑了?”
冯县令事实上肚子没啥墨水,到是这位师爷不简单,经常能给他好的主意。
耳濡目染,冯县令说话也文绉绉,不清不楚,含糊其辞。
师爷立马拦住:“大人不可。
刘夫子走前交代过,不要为难那孩子,上面的人怎么不做,与我等无关,那是为刘夫子铺路。但是咱们不同,万一此去京城,刘俞舟一飞冲天,事后追究起来,我们无法交代。”
“那便让这块肥肉,就这般隔着?便宜了那几家?”冯县令不解的问道。
“自然不是,大人不若以县衙的名义派人去保护那孩子,他要是炼化了那东西,我等便是大力相助;若是时运不济,资质不够,大人正好以县衙名义,将东西拿回来暂时保管,一来,没有违刘夫子的约,二来,也免得落入其他几家手里;之后,等京都的事情尘埃落定,再做决定不迟。”
冯县令听的大喜,现学现用:“不错不错,便以刘夫子的名义,将其保管起来。”
他很快找人吩咐了下去,言语当中,多有偏袒。
师爷叹了一口气,冯县令什么都好,就是贪财了一些,不管什么,只要能换钱就行,要不,怎么和城里贾商关系最好。
官何曾能兴于商,都是商依附于官。
....
....
刘夫子背着包袱赶路,他始终惦记弟子宋孝廉死前的话。
从背上带着的包袱里随意取出一本书,翻开一页。
是先秦著作六韬中一本。
上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我此去京都,何尝不是一种利益交换,蜗居北地,著书修心,但求心行合一,今有疑问,何不停留数日,想必老师知道了,也不会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