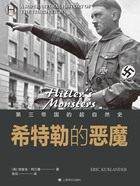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纳粹主义的超自然根源
雅利安-日耳曼宗教、边缘科学与奥-德神秘学的复兴,1889—1914
“一旦驯服的护身符十字架一断为二,古老战士的蛮荒勇力,北方诗人所歌唱的狂暴战士的无情怒火……就会再次喷涌而出……古老的石神就会从寂静的废墟中腾起,而……雷神就会挥动他的巨锤,纵身一跃,将哥特人的教堂化为齑粉。”
——海因里希·海涅(1834),兰茨·冯·利本费尔斯引用(1907)(1)
“在德国,潜意识的恢复……为德国式的20世纪独裁统治打下了基础。这种反应将德国浪漫主义的深层暗流与玄学的神秘以及行为的理想主义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行为最终将血淋淋地写在历史的页面上。”
——格奥尔格·摩瑟,《大众和人》(1987)(2)
1909年8月的一天,一个年轻人来到奥地利神秘学家约尔格·兰茨·冯·利本费尔斯在维也纳的办公室。来人面色苍白,衣着破旧,他颇有礼貌地介绍了自己,并问是否可以买几本兰茨自己出版的杂志《奥斯塔拉》(3)的过刊。兰茨在中欧地区不遗余力地推广“雅利安智慧学”,这种深奥的学说预言北欧“神人”创造的业已失落的雅利安文明会重现世界。照兰茨的说法,他的《奥斯塔拉》杂志是“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种族科学杂志……与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革命者做斗争,维护高贵的雅利安种族不致衰落”。来人的样子令人同情,举止诚挚,感动之余,兰茨免费送了那人几本《奥斯塔拉》的过刊,还给了他两个克朗,让他坐有轨电车回家。照兰茨1951年的回忆录所说,来人正是阿道夫·希特勒。(4)
由于是40年后写下的,兰茨的这番回忆有可能是杜撰的。他对自己和希特勒有过交集感到自豪,而且,考虑到他的神秘学倾向,很难成为一个可靠的信息源。但有大量的与此有关的证据表明兰茨的故事是真的。(5)只要阅读任何一期《奥斯塔拉》,未来的元首都能遇到几个主题,十年以后,这些主题就会被纳入纳粹党的大计:“北欧”血统纯洁的重要性,种族混杂的危险性;“犹太人”可怕的背信弃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有害影响;印欧纳粹万字符的神秘力量。兰茨坚称,只有谨遵秘传的宗教和优生学实践,包括消灭犹太人、给低等种族绝育,才能使北欧文明再次苏醒。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兰茨在《奥斯塔拉》里画了许多生动的插图,描绘肌肉发达的雅利安骑兵保卫衣不蔽体的金发女性免受长相丑陋、“尖嘴猴腮”之人的侵犯,这些都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纳粹宣传中常用的比喻。(6)
当时,希特勒住在菲尔博路的一间小公寓里,靠画水彩明信片消磨时间,所以很容易想象年轻的希特勒会迫不及待地吸收兰茨宏大的种族主义宇宙学,在这个宇宙学中,世界一分为二,一明一暗,金发碧眼的北欧英雄在和“低等人种”(7)进行着永恒的战斗。(8)到1909年,未来的德国元首已经沉浸于兰茨信奉的更广泛的种族子文化之中。希特勒看了几十次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奥地利政治家格奥尔格·冯·舍纳勒的种族主义和泛德意志思想。他还对长期担任维也纳市长的卡尔·吕格(此人也是雅利安智慧学秘密社团的一员)极具煽动性的反犹言论颇为赞赏。
希特勒在这方面也很典型。他那一代人到20世纪之初都已成年,其中许多人都对“神秘的乌托邦复兴”心向往之。(9)对于广大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来说,神秘主义和边缘科学、北欧神话和新纪元实践、种族宗教和日耳曼民间传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提供了一种另类启蒙形式,有望照亮宇宙的最深处和灵魂的最深处”。(10)这些超自然的理念和学说纷繁多样,可塑性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十年内获得了数百万非常现代、具有远见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支持。(11)
第一章的目的是描述一战后将被纳粹“吞下”的超自然理念和实践方式。(12)尽管这些理念非常灵活,彼此勾连,但仍可松散地分为三个重叠的子文化。第一个是雅利安-日耳曼宗教、民间传说和神话。第二个是神秘主义,包含秘术和神智学、人智学、雅利安智慧学。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边缘科学”,从占星术、超心理学、射线探测术(“探测术”)到“冰世界理论”,不一而足。
这些子文化在纳粹主义的兴起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从意识形态的内容来看,这三个子文化都传播和普及了一些激发纳粹的超自然想象的理念和学说,并给更广泛的纳粹选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次,这些子文化使秘术和边缘科学的方法合法化,使人能对以纳粹的种族和空间、科学和宗教思想为特点的世界有更好的了解。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看一看“漫长的19世纪”,也就是1789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雅利安-日耳曼宗教、民间传说和北欧神话的复兴。然后,我们将转到19世纪最后30年奥-德神秘学的复兴,重点关注1880年代到1910年代这30年时间。最后,我们会考察在同一时代作为一个合法研究领域平行出现的边缘科学,追溯上述三个子文化——雅利安-日耳曼宗教、神秘主义、边缘科学——在奥-德超自然想象的兴起过程中互相强化的方式。
一、雅利安-日耳曼宗教、民间传说和北欧神话
马克斯·韦伯在1917年关于“作为职业的科学”的演讲中,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们时代的命运是以理性化和智识化,更重要的是以世界的祛魅为特点的。”(13)这个说法经常被引用,成为19世纪末宗教衰落和科学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证明。可是,学者们往往忽略了韦伯的下一句话:“确切地说,终极和崇高的价值观已经从公共生活退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退入兄弟情谊这一个体和直接的人际关系之中。”(14)
现代世界可以被定义为对传统宗教的祛魅。但同时一种新形态的日常宗教精神也在复兴。这种对神话的渴求,对命运和奇迹的重新信仰都发生在传统宗教体制的框架之外。(15)尽管1890年代以来上教堂礼拜的人数急遽下降,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还是在继续寻求意义和灵性,只是和主流基督教不同,不再需要教会居间,也没有什么宗派之分。(16)
为了创建并巩固德意志第二帝国,知识分子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让古代的神话和英雄起死回生。他们探索了印欧历史和宗教,寻求一种浪漫主义的东西来替代许多德国人认为过度理性化的法国文化和过度冷漠的英国实用主义。正如恩斯特·布洛赫在第三帝国初期所说,神话和种族宗教为法西斯操控民众提供了工具。(17)如果不是因为在漫长的19世纪,这些理念得以复兴,实际上是(再)创造,那么1920年代和1930年代纳粹在政治上利用这些理念将是不可能的。
对神话的渴求
早期浪漫主义作家激起了德国人民族情感的第一次萌动。其核心就是德国民间传统和神话受到了重视。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是最早借用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超自然人物作为主人公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如《科林斯的新娘》里的吸血鬼,《魔王》里的精灵国王。与此同时,歌德也和弗里德里希·席勒一起哀叹德意志祖国的缺失。(18)
歌德和席勒的同时代人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从古代日耳曼的民间故事和北欧人的神话中寻找德意志民族的根源。赫尔德说:“诗人就是他置身其中的民族的创建者,他手中拥有那些人的灵魂,可以引领他们。”(19)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告德意志同胞书》中,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在《德意志祖国》(The German Fatherland)这样的诗中,用一种近乎神秘的种族观念来充实那些想法。弗里德里希·谢林则认为,是灵性上的差异将德意志人这样的高等种族和低等种族区分了开来。(20)
以格林兄弟和瓦格纳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浪漫主义作家、音乐家、艺术家,采用德意志的民族主义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纷繁叙事来为广大的公众创作作品。(21)40年里,威廉·格林和雅各布·格林辛苦收集,出版了大约200个童话故事,帮助重建了实实在在的“日耳曼”(或“雅利安”)文化、语言和身份。与法国和英国的童话故事相比,格林兄弟的故事更暴力,更异想天开,(无疑)也更具有种族主义色彩。他们描绘的世界充斥着超自然的怪物,如食人巫师和诡计多端的魔法师,居心叵测的犹太人,复仇心切的精灵,变幻多端的野兽,善于操控的妖怪,还有魔鬼本人。(22)然而,从格林兄弟到希特勒的德国民族主义者都会盛赞这些故事为德国的种族思想打下了基础。(23)到1857年,瓦格纳已经创作出了《莱茵的黄金》的大部分内容,这是《尼伯龙根的指环》四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余几部是《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诸神的黄昏》。《尼伯龙根的指环》对北欧传说大体进行了重构,对普及德意志的民族神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希特勒本人的雅利安-日耳曼意识形态图景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24)在《尼伯龙根的指环》中,主人公齐格弗里德与沃坦和洛戈几位神必须抵御邪恶的尼伯龙根,这一暗黑的种族从莱茵仙女那里偷走了黄金,打造出了一个拥有统治世界的力量的魔戒。(25)
瓦格纳和格林兄弟推广日耳曼民间传说和神话的努力的基础,是对卢恩字母(runic alphabets)、死语言、古代文本的恢复,有时候干脆是发明。北欧传说、卢恩字母和童话故事都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甚至会包含魔幻意义,从而成为“种族的根源和本质”至关重要的表达形式。(26)比如,19世纪中后期,人们对中世纪冰岛散文诗《埃达》(Edda)的兴趣普遍恢复,这部作品对北欧诸神和英雄的功绩做了逐年记录。(27)到1900年,北欧神话的复兴体现在许多种族协会和期刊的名字上,比如《奥丁》、《海姆达尔》、《锤子》、《雄柱》、“日耳曼骑士团”以及泛德意志语言和写作协会。(28)
民间传说、神话和新异教信仰争相填补德意志精神景观的一大重要缺口,以助力占领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清空的“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29)当有些种族论民族主义者想要将德国的天主教徒从“罗马解放出来”时,另一些人则试图将德意志异教信仰和基督教结合起来。还有一些人走得更远,认为基督教当以“基于自然的世界宇宙精神”马首是瞻。(30)
纷繁复杂的“德意志基督徒”、“德意志宗教人士”、“德意志信仰运动”的支持者以及“新异教徒”在许多教义上存在分歧。但这些想法吸引了大量“致力于创造适合德意志种族的新宗教的男男女女”。(31)所有这些团体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用更具“日耳曼特色”的宗教信仰来取代传统基督教。(32)
除了对民间传说、神话和替代的宗教感兴趣之外,狼人和女巫也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基督教礼拜仪式中的这些恶魔如今越来越被视为积极的形象。威利巴尔德·阿列克西斯的《狼人》(Der Werwolf,1848)出现在德国和奥地利爆发民族革命的那一年,而赫尔曼·伦斯的《狼人》(Der Wehrwolf,1910)则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这两部作品均以近代早期的宗教战争为背景,当时,德国农民想要保护自己不受反宗教改革的军队的侵犯。这些作品所描述的“狼人”并不是怪物——至少不是邪恶的怪物——而是英勇的游击队抵抗战士,他们发誓要捍卫德意志的血脉和土地不受外国侵略者的侵扰。(33)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巫术也在新的民间传说中得到重新阐释。德国的“女巫”不再是撒旦的爪牙,而是地母、古代印度-日耳曼宗教的践行者,这种宗教是天主教会想要根除的,天主教会的裁判官才是真正的恶魔。(34)在19世纪的超自然想象中,魔法和巫术的传统有时候会和德意志异教信仰中的摩尼教支流相结合,后者认为路西法是个正面人物,“被不公正地赶出了天堂”。(35)数千名德国中产阶级人士蜂拥前往布罗肯山和伊克斯坦岩(Externstein),前者是歌德的《浮士德》中“瓦尔普吉斯之夜”(Walpurgisnacht)的所在地,后者是异教遗址。(36)后来的神秘主义者和许多纳粹分子都接受了这种“路西法”传统的各个方面。
1850年后,我们发现对现代早期菲默法庭(37)的兴趣也在平行增长。这个据说被视为禁止的(verbotene)或秘密的(geheim)法庭,是由威斯特法伦乡村特定地区的当地名人偷偷摸摸召集的,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自己充当法官、陪审团、行刑者的角色。启蒙时代的改革人士抨击了该法庭,最终在19世纪初被热罗姆·波拿巴(拿破仑最小的弟弟)宣布为非法。但是,后来民间又重新燃起了对原日耳曼时代秘密法庭的兴趣。(38)几十年后,秘密治安民团处死德国敌人的传统被右翼狂热分子拿来使用,后者意图在魏玛时代初期杀害犹太政客和左翼政治家,这种做法被称为政治谋杀(Fememord)。(39)
在法国和英国,吸血鬼被视为哥特文学的奇珍,甚至是悲剧性的浪漫主义形象。在讲德语的中欧地区,吸血鬼则是更为邪恶的形象。(40)德国对斯拉夫腹地吸血鬼的报道更是强化了一种超自然的观点,即“波兰人[以及后来的犹太人]危险”,认为那是一种玷污了“纯日耳曼种族起源的风景”的生理和心理疾病。(41)相邻的波希米亚如今已是“吸血鬼的诞生地,塞尔维亚[数以万计的德裔人口就定居在那儿]成了蛮子的家园,波兰则成了迷信的聚集地”。因此,斯拉夫的吸血鬼形象就成了种族退化和“普鲁士-德国和奥匈帝国边境地区多民族关系”从政治上瓦解的隐喻。(42)
种族退化的斯拉夫(犹太)吸血鬼和英勇的“雅利安人”棋逢对手。(43)“雅利安”种族高人一等的观念可以从19世纪早期印欧的复兴中找到根源。(44)法国人阿蒂尔·德·戈宾诺及其著作《论人类种族之不平等》(Inequality of Human Races,1855)在欧洲全境广受欢迎。40年后,英国出生的亲德者、政治哲学家、瓦格纳的女婿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在其两卷本的著作《19世纪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赋予了这个观点“科学”的合法性。(45)
对张伯伦而言,整个欧洲史都可以归结为英勇的雅利安人和恶魔般的闪米特人的统治权之争。张伯伦认为,“雅利安人”寻求的是更高等的知识和被优越的“种族灵魂”激发出来的更高的创造力。相较之下,犹太人就是摧毁文明的唯物主义者,缺乏超验的能力。(46)
这种混合了种族、宗教、神话的超自然大杂烩中有一个时常被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印度-雅利安人种。(47)许多浪漫主义者在对德国文化中经典的犹太-基督教基础提出质疑时,赞颂了非西方文明的美德。莱辛和赫尔德是第一批强调德国文化中的“东方”、前基督教根源就在印度北部和中东地区的人。(48)
后来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如施莱格尔兄弟,将犹太教和基督教同印度-日耳曼雅利安人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糟糕。他们认为,罗马天主教和福音教会喜欢“开疆拓土”,相较之下,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更开明。(49)许多德国民族主义者都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持这种欣赏的态度,它将贯穿19世纪余下的时间,后来还将在第三帝国引起令人惊异的共鸣。(50)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早期的浪漫主义推测又得到了德国印度学这一新兴学科的滋养。德国的印度学学者在研究印度文明和宗教的时候,从中发现了雅利安文化和精神的本质理念的证据。(51)著名的梵文学者利奥波德·冯·施罗德就是瓦格纳的信徒,也是张伯伦的雅利安文明和种族退化理论的支持者。施罗德希望将印度文化和宗教推广至德国全境,“借用佛教的主要观点来畅想未来的宗教”。(52)
其他印度学学者,如老阿道夫·霍尔茨曼和小霍尔茨曼将“印度-日耳曼[英雄]史诗”,即“原始史诗”(Ur-Epos)中的奇思异想投射到了《摩诃婆罗多》和《薄伽梵歌》之类的印度宗教文本上,但这么做等于剥离了文本和语言学的证据。这些学者将《摩诃婆罗多》比作北欧的叙事诗《尼伯龙根之歌》,将古印度与前基督教时代的日耳曼文明相比较,这些学者得出来一个强有力的说法,即《薄伽梵歌》就是“反映印度-日耳曼英雄主义观的泛神论文本”。(53)
这些对印度教和佛教文本的选择性阅读,将受到诸如J.W.豪尔和瓦尔特·伍斯特之类的纳粹印度学学者的大力提倡,为的是证明雅利安种族在人种文化上的优越性。(54)印度-雅利安人种尽管具有世界大同主义的性质,却在德国的“神秘的乌托邦复兴”和“对神话的渴求”中煽动起了更为黑暗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倾向。(55)
有意识地将民间传说和神话、印度-雅利安宗教及种族理论融入德国的儿童教育之中是重要的步骤,可以从小灌输德意志民族情感和精神感受。(56)那么,高中历史老师利奥波德·珀奇博士向希特勒及其同学介绍“日耳曼历史上的史诗时代”——里面充斥着雅利安英雄和低级的恶魔,“尼伯龙根、查理曼大帝、俾斯麦,还有第二帝国政府”——也就不是什么巧合了。(57)到19世纪末,民间传说、神话、雅利安-日耳曼宗教热忱已不再是浪漫主义时代少数几个知识分子的鲜为人知的苦思冥想,而是深深地烙印在了数百万普通德国人的意识之中。
日耳曼主义,雅利安人种和地缘政治
正如克里斯·曼加普拉所注意到的,上述印度-雅利安种族理论和“建立在[恩斯特·]布洛赫所谓的虚幻乌托邦追求之上的激进的反殖民主义”之间,“有可能存在亲缘关系”。(58)1871年之前,德国人缺少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或殖民帝国。这种民族主义渴望与之前就存在的“对神话的渴求”相结合,就产生出了印度-雅利安种族纯净性的乌托邦概念。虽然在批评英国对印度的压迫时看似是反殖民主义的,但这种印度-雅利安兄弟情谊的乌托邦愿景背后的神奇思维,使德国人难以填满自己的种族与殖民幻想和地缘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通过这种方式,关于恢复一个失落的印度-雅利安文明的超自然幻想不仅产出了“解放的潜力”,也生发出了“报复”和“种族灭绝”。(59)
若想理解这种印度-雅利安的“解放神学”在纳粹超自然想象之中的作用,我们就需要了解这些思想在世纪末的种族论知识分子中间是如何同政治一起孕育起来的。(60)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把19世纪后期充斥着种族论、准宗教性质的民族主义的主要践行者称为“对文化绝望的政客”,这么说也许并不公平。斯特恩认为,这些反现代的知识分子将激进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神秘学同面向未来的乌托邦理想结合了起来,而这种乌托邦理想是拒斥科学唯物主义和工业化的。(61)
这些知识分子的反文化和悲观主义特质被过于夸大了。许多渐进式改良主义者,如马克斯·韦伯和格特鲁德·鲍默尔,也同样对快速现代化和工业化对德国社会的冲击感到“绝望”。相反,博学的东方学家保罗·德·拉加德和另一些人,尽管有浓烈的种族论色彩,但也是文化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62)事实上。拉加德是德国研究近东语言和宗教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发行范围最广,本人也极受尊敬,他对印度-雅利安文化非常痴迷,我们发现他也出现在了奥-德超自然的圈子内。(63)
尽管(或者也许是因为)拉加德浸淫于“印度-雅利安”和中东研究,但他也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预见了后来的种族论思想家的计划:德国需要有本民族的基督教,需要建立于雅利安种族之上的印度-日耳曼大帝国,需要强烈的反犹主义种族仇恨,如有需要,其中应包括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不消说,像伍斯特、H.K.君特之类的一些纳粹种族主义理论家和印度学学者,以及像希特勒、希姆莱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这样的党政要员,都受到了拉加德著作的影响。(64)
1890年,拉加德的同代人中比他年轻的作家、文化批评家朱利乌斯·朗贝恩出版了广受欢迎的《作为教育者的伦勃朗》(Rembrandt as Educator)一书。在这本书中,朗贝恩将包含全体“雅利安”人在内的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观点,同他极其虔诚而极不正统的天主教信仰结合在了一起。(65)朗贝恩声称,“神秘主义乃是隐藏的引擎,可将科学转变成艺术”,“德国只有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情况下才会长足进步”,“确实拥有土地的农民和地球的核心有直接的关系”。(66)这种对嵌入其土生土长的家园(Heimat)之中的种族上和精神上纯洁的德国农民进行神化的做法,成了世纪末种族论(以及后来的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因素。(67)
像阿道夫·巴特尔斯、阿尔弗雷德·舒勒、穆勒·范登布鲁克这样的种族论知识分子,将这些思想带入了20世纪。巴特尔斯在将拉加德和朗贝恩的观点推广开来的过程中,成为德意志帝国晚期最重要的种族论出版人之一,其中包括一本有16篇边缘科学论文的文集,书名直接定为“种族”。巴特尔斯还和种族论神秘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利恩哈德合作,创办了《日耳曼家园》(German Heimat)杂志,推广人种和空间的种族-秘术概念。(68)
担任“宇宙圈”(cosmic circle)这一慕尼黑秘术团体负责人的阿尔弗雷德·舒勒,在拉加德的印度-雅利安人种、兰茨的神秘主义、朗贝恩的“血与土”哲学之间架起了桥梁。(69)对舒勒而言,一个人的“内在生命力等同于其血液的力量”,神秘主义的纯洁性据说会因种族混血而退化。他相信拥有超心理学和灵性力量的“未受玷污”的雅利安人,会在“血之灯塔”和万字符这一神圣象征的旗帜下恢复种族的纯洁性,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他还和慕尼黑超心理学家阿尔伯特·施伦克-诺青格(下文将会讨论)合作举行了降神仪式。舒勒宣扬诺斯替教(摩尼教)、卡德尔教派(14世纪法国的一个基督教异端教派)的宗教传统以及亚特兰蒂斯的雅利安智慧神话之间具有关联。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这些聚焦雅利安血脉的神秘力量及圣洁性的主题就被许多纳粹思想家拿去用了。(70)
范登布鲁克比舒勒更卖力,他主张将日耳曼基督教和异教信仰、种族论民族主义和德国式社会主义混合起来,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场政治革命。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23年出版的《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希特勒就是在这一年想要推翻魏玛政府,只是没有成功。(71)范登布鲁克预言未来会发生一场战争,生灵涂炭,文明重生,他那预言式的民族主义同威廉时代后期的科幻小说可以说是水乳交融。其中值得注意的有纳粹地缘学说专家卡尔·豪斯霍费尔的父亲马克斯·豪斯霍费尔的《星球之火:未来小说》(Planet Fire:A Futuristic Novel,1899),费迪南德·格劳托夫的《1906年:旧秩序的崩溃》(1906:The Collapse of the Old Order,1905),后者在出版后的头两年里卖出了12.5万本。(72)
泛德意志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的著作,也在主流学术和宣传德意志种族与帝国的神秘投入之间摇摆不定。在19世纪末的这些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或许当属弗里德里希·拉采尔,他是“生存空间”(Lebensraum)这一声名狼藉的概念的始作俑者。
和上述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拉采尔对追随英法两国的做法向海外殖民持相对敌视的态度。(73)拉采尔相信,这么做就会让数百万其他种族的非洲人和亚洲人进入帝国,使得德国丧失在人种上和领土上的完整性。拉采尔反倒是希望通过“内部的殖民化”过程,也就是将德国农民的农业技术和民间传统扩展至东欧的“生存空间”,创建一个共襄盛举的大德意志帝国。(74)
拉采尔基于信仰的生存空间概念没法进行科学验证。但这样事实上使德国对中欧和东欧地区的任何干预都变得合情合理。而且,这也提供了一套模板,将德国的人种学和民间传说当作工具,为扩张服务。(7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生存空间”的需求已成为在许多种族论思想家中间流行的修辞手法。(76)
确实,拉采尔的“生存空间”概念为催生“地缘政治”这一极为流行的学科出了力,他的学生卡尔·豪绍弗尔在第二帝国的最后十年里使这一学科闻名于世。豪绍弗尔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形式”,需要不断地拓展边界以维持其种族和文化生命。(77)通过他在慕尼黑大学的学生鲁道夫·赫斯的引荐,豪绍弗尔成了希特勒早期对外政策的顾问之一。(78)
所有这些种族论知识分子和地缘政治学家都为定义种族和空间的边缘科学概念出过力,而正是这些概念激发了希特勒和纳粹运动。(79)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有助于解释纳粹自身的超自然想象中的一些矛盾之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日耳曼性”(Germanentum)和“雅利安人种”(Ariertum)之间的紧张关系。
从1890年代开始,日耳曼性的支持者如语言学者安德烈亚斯·休斯勒、考古学家古斯塔夫·考希纳,就倾向于将注意力放在朱利乌斯·朗贝恩笔下的北日耳曼民间传说的文化天赋上。“北欧”版的日耳曼性对区分日耳曼种族和犹太人及斯拉夫人非常有用,并且为更“奇异的种族论思想要素”提供了科学的外表。“以瓦格纳和[圭多·冯·]李斯特为代表的更为诺斯替的方面被学院派的日耳曼主义者削减之后,日耳曼性这一意识形态便和‘[后来的纳粹优生学家]H.K.君特的北欧种族主义’”以及“研究东方的新专家对帝国主义的思考”“完美契合”,一战之后,他们都和纳粹党进行了合作。(80)
除了以北欧和西欧为中心的种族层面的北欧日耳曼性之外,19世纪末还出现了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即“雅利安文化明显植根于印欧比较研究之中”,这个概念受到了戈宾诺、张伯伦、拉加德以及19世纪末印度学学者的启发。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雅利安人种”,还是“日耳曼性”,都只是变种而已,两者同样信奉原日耳曼人这一占主导的种族。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概念“被万字符象征性地联系在了一起”,像考希纳这样的日耳曼学家就对北欧文明的印度-日耳曼(雅利安)根源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81)
但雅利安人种既超越了日耳曼性这个狭义的概念,也将这个概念包含在内,它为更具扩展性和包容性的印度-雅利安种族及帝国概念奠定了基础。“到了1910年代,雅利安人不仅是一种人类学的表述,”伯纳德·米斯说,“它还被一些德国和奥地利作家提升为一种文化身份。这些学者、伪学术爱好者,甚至耽于幻想的人都属于雅利安潦倒文人圈,像[圭多·冯·]李斯特及其追随者之类的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者只不过是其中最五彩斑斓的部分而已。”(82)
奥丁崇拜的哥特人这一狭义上的日耳曼神话和“雅利安潦倒文人圈”之间存在与科学完全无关的差别,这个差异将一直存在于第三帝国内部。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重要的差异,纳粹的边缘科学家之间才会爆发一些政治争论和意识形态争论。(83)不过,大多数纳粹分子,包括希特勒和希姆莱,似乎都更倾向于拉加德那种更宽泛、更具包容性、更具延展性的“雅利安人种”之说,而不是朗贝恩那个限制性太强的“日耳曼性”。(84)
这些对日耳曼种族和宗教所作的看似晦涩难懂的讨论不应模糊它们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艺术史学家弗利茨·萨克斯尔写道,19世纪末,雅利安-日耳曼宗教、民间传说、神话的复兴一如12世纪的复兴,那个时期,“基督教似乎已无法完全满足人类的灵性层面,异教信仰就有了渗透的空间,这和我们如今看到的情况一样”。卡尔·荣格将异教信仰和神话重新引起的兴趣同中世纪后期层出不穷的诺斯替派异端邪说进行了对比,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这种比较颇具先见之明。(85)
最终,这些民间传说、神话、雅利安-日耳曼宗教的支持者合力竖立了“一个与后世北欧的‘战士灵魂’相得益彰的高贵而闪亮的信仰”。照刘易斯·斯宾塞的说法,他们“把所有原始和混乱的异教信仰强加给德国……这些异教信仰都是在《老埃达》和《小埃达》这两部福音作品里找到的,再加上他们对这些学说的一知半解,似乎这样就免得被人指责为剽窃或缺乏理性”。(86)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纳粹将以这些民间传说、异教信仰、神话为基础,寻找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替代品,在亚洲建立地缘政治上的联盟,创建一个种族纯正的日耳曼人帝国。
二、奥-德玄学的复兴
最重要的德国神秘主义专家科琳娜·特莱特尔写道:“神秘(Occult)这个词来自拉丁语动词oewlere,意思是隐藏或掩盖。因此,有那么点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德国人对人类的视力不可见或理性无法知晓的力量倍觉痴迷,但德国的神秘学运动自身并没有特别藏头露尾。”(87)从世界都会柏林到天主教的慕尼黑,从萨克森州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成千上万德国人蜂拥而来参加降神会,来见占星师、塔罗牌占卜师,参加超心理学实验,逛神秘学的书店,甚至去上秘术学校和大学课程。(88)
当然,神秘学的复兴并没有局限于德国。我们有大量证据显示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有相似的趋势。(89)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多样性来看,都表明德国和奥地利神秘学市场已经融入大众消费文化,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这种文化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独一无二的。单单柏林和慕尼黑就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巫师、灵媒、占星师,吸引了数十万的消费者。(90)
重要的是,提倡神秘主义的组织和出版商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不拘一格的。他们糅合了“各式各样的政治立场、文化风尚和社会纲领”,反映了“随着现代主义创新的兴起,德国人在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纪元的要求”。(91)但尽管如此,“在有些情况下,神秘学和种族论的文本也都来自同样的出版物”,只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神秘主义者都持有这些种族立场,也不意味着所有的种族主义者都会接纳神秘学或神秘主义的态度。
但现实情况仍然是“许多出版物都介于德国现代主义的神秘学和种族论的曲调之间”,而这种关联在英国或美国的背景中就没有这么突出。(92)弥漫在奥-德超自然界的典型的现代性和“新纪元”要素,与怪诞的种族理论以及瓦格纳、朗贝恩、拉加德等人虚幻的种族理论和雅利安-日耳曼神话彼此交缠。(93)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30年里也能看出,人们对于将占星术和招魂术同新异教及政治结合在一起的神秘学-共济会团体的兴趣再次抬头。以自由主义和英—法为基础的共济会广为人知,这就解释了欧洲全境的天主教和民族主义保守派为什么会产生反共济会的情绪。然而,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共济会会员从观点上看并不都是一成不变的自由主义者或世界主义者。讲德语的中欧地区也并不缺乏从条顿骑士团和玫瑰十字会(94)而来的共济会及骑士团的保守传统。(95)
紧随上述异教和神话的复兴而来的是种族-秘术团体,这些团体以德国和奥地利全境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共济会为模板,它们通常从更广泛的神秘学运动中脱颖而出,如神智学和雅利安智慧学。其中一些秘密社团包括阿尔玛恩骑士团(Armanen-Orden)(96)、新圣殿骑士团(Ordo Novi Templi),以及日耳曼骑士团(Germanenorden),在纳粹党早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97)
神智学和人智学
俄裔德籍贵族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发明的神智学,是19世纪末影响最大的神秘学学说。布拉瓦茨基曾在印度和西藏地区旅行,颇受启发,于是1875年在纽约创办了第一个神智学协会。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布拉瓦茨基发展了这一运动,包括在德国和奥地利赞助成立分会,还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秘密学说》(The Secret Doctrine,1888)。(98)兼收并蓄的两卷本《秘密学说》充分吸取了达尔文主义、印度教、藏传佛教和埃及的宗教。它还抄袭了爱德华·布威-利顿的奇幻小说《即将到来的种族》(The Coming Race,1871)中的情节,该小说描述了一个可以操纵名为维尔(99)的魔力的强大地下种族。(100)
依照布拉瓦茨基的人类进化的神秘学理论(anthropogenesis),人类共有七个“根种族”(root races)。从作为宇宙能量的种子开始,人类经历了不同的进化阶段,包括许珀耳玻瑞亚人(101)、雷姆利亚人(102)和亚特兰蒂斯人,然后才能达到目前的灵与肉的发展阶段。由于人类的不同分支保留了这些原始根种族的不同痕迹,所以现代人类在生物和精神的禀赋上都会有所不同。雅利安人仍然享有在地的自豪感,只是他们已经丧失了“东方民族”仍旧享有的魔力。隐身的领袖,或者布拉瓦茨基通过心灵感应与之交流的神智运动的“圣雄”,被称为“伟大的白人兄弟”。(103)
正如有些人所说,神智学并没有彻底拒绝启蒙运动或“脱离理性”。(104)典型的世纪末神秘主义的神智学,确实在努力将自然科学和超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结合起来,对工业时代的精神困境给出“现代”的答复。尽管神智学含有令人生疑的种族主义要素,易被诟病为招摇撞骗之术,但它也提倡一种进步的世界性的信仰,即想要使“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性别、等级或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105)德国的神智学运动激发了人们对占星术、诺斯替主义、犹太教卡巴拉以及基督教神秘主义和印度与中国西藏智慧的兴趣。(106)欧洲各地和北美地区的神智学也致力于印度独立、动物权利、素食主义和性解放等事业,这些理念和保守的民族主义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107)
尽管如此,神智学思想的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面向,如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监狱改革、和平主义,或许在英国人中要比在奥-德的分支更强烈。(108)吊诡的是,印度宗教、动物权利、素食主义、性解放这些理念在种族论秘术和后来的纳粹圈子里也是重要的元素。
神智学和其他神秘学说一样,也具有延展性和矛盾性,糅合了“种族的生物和精神的概念,经常没什么条理性”。科琳娜·特莱特尔说:“神智学家可以坚称一个人所属的种族主要与其精神成熟度有关,但同时又声称,像印度北部雅利安人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已经达到了特别高的精神成熟度。”(109)尽管神智学痴迷于东方宗教,声称“四海之内皆兄弟”,但其让“第六个根种族”存于世的目标,才是神智学运动的核心,尤其在奥-德分支是如此。(110)
失落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或修黎(111)在神智学世界观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得不提。(112)失落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据说是神圣(有可能是天外)种族或精神上的完美的史前来源。对布拉瓦茨基及其追随者而言,亚特兰蒂斯或许和神秘的佛教圣地“香巴拉”以及印度教传统中雅戈泰(Agarthi)的都城有关,显然就在喜马拉雅山底下,第三个根种族雷姆利亚人的后代就居住在那儿。(113)后来纳粹去中国西藏探险(见第六章)根源就在这些地缘政治观和历史观上,这些观点都来自布拉瓦茨基及被她剽窃作品的爱德华·布威-利顿,两人都强调了中国西藏智慧的重要性以及中国西部和印度北部的种族在进化上的优越性。(114)
后来,对布拉瓦茨基的观点进行阐释的奥-德人士,尤其是兰茨和李斯特,都将亚特兰蒂斯视为北大西洋岛屿的修黎文明。修黎是名为许珀耳玻瑞亚的原始雅利安文明的都城,其北欧遗存或许可在如今的黑尔戈兰岛或冰岛见到。兰茨和其他人相信,全球大洪水将这古老文明摧毁之后,屈指可数的幸存者应该是迁徙到了喜马拉雅山的高处,在那儿建立了雅戈泰秘密社团。(115)神智学认为,已经失传但可以恢复的雅利安文明起源于印欧史前时期,这一观点在其他神秘学理论和边缘科学理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透过雅利安智慧学和“冰世界理论”,原始雅利安亚特兰蒂斯(修黎)的想法就这样进入了纳粹关于种族与空间的理论之中。(116)
布拉瓦茨基的神智学运动很快就在德国和奥地利各地收获了支持者,沿途还将更多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元素整合了进去。1884年创建德国神智学学会的威廉·胡伯-施莱登就是这些倾向的例证。胡伯-施莱登出身汉堡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便活跃于殖民地贸易领域,1875年移居非洲,在加蓬开了一家商行。他对种族和空间的神秘主义倾向受到了他在非洲的经历的影响,激励他成了神智学和德国帝国主义的早期支持者。在胡伯-施莱登的心目中,在德意志帝国传播的神智学可以为改良这个世界提供一种工具,在这个世界上,“现有的人类种族——进化程度更高的雅利安人和进化程度较低的黑人及蒙古人——将学会在一个更为团结、精神上更高端的文明中如何通力合作。”(117)
作为19世纪晚期的文化批评家的典型代表,胡伯-施莱登一方面主张用神智学来与传统基督教会的“自我瓦解”进行抗衡,另一方面主张“感性的唯物主义和无脑的快乐只是猎奇”,现代生活的“道德和精神都在腐坏”。神智学可以为一个崭新的、不那么支离破碎的、更完整的个体提供基础,这种社会改良观点是以社会阶级之间的精神冲突而非其物质冲突为开端。(118)
据说,胡伯-施莱登曾从一位强大的圣雄那儿收到一封神秘的信件,受此启发,他花了数年时间试图“为神智学的精神教诲提供科学依据”。他在自己的公寓里摆满了精心制作的奇特的金属丝装置,以此来代表展现神智学的超验体验的分子链。(119)简而言之,胡伯-施莱登身上反映出了世界主义和种族主义、科学和秘术元素的独特混合了起来,而这些正是奥-德超自然想象的特点。(120)
1887年创建了首家奥地利神智学会的弗朗茨·哈特曼采取了稍微不同的路数。但他的观点也同样是将种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科学和超自然糅合在了一起,这一点对许多纳粹分子很有吸引力。(121)和布拉瓦茨基与胡伯-施莱登一样,哈特曼之所以走上神智学这条道路,也是因为他真诚地想要找到一个新的学说,可以将科学思想和超自然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和希特勒、赫斯、希姆莱一样,哈特曼也逐渐背弃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他欣赏教会的仪式、神秘主义、灵性,但拒斥教会的教条主义和等级制。哈特曼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医生,接受了现代医学的某些层面。然而,他在许多纳粹分子之前就批评医生过于依赖从生物学角度来治疗疾病的做法(比如,他认为接种疫苗就是一种“恶行”)。(122)
哈特曼接受布拉瓦茨基的邀请,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灵性实验,之后,他成了一名神智学家。(123)和世纪末的神秘学界一样,哈特曼的社会交往也是五花八门。他和犹太神秘主义者、“生命改革家”弗里德里希·埃克斯坦走得很近。他也很欣赏激进的种族主义者、反犹的雅利安智慧学家圭多·冯·李斯特(见下文),哈特曼还赞扬了此人那怪异的且并不科学的卢恩文字研究。(124)
哈特曼的神智学同行鲁道夫·施泰纳是经由埃克斯坦领导的维也纳神秘学圈子进入神智学领域的。(125)在花了好几年时间寻找一条介于科学唯物主义和宗教之间的道路之后,他加入了神智学社团,因为神智学发现了高于所有宗教的“真理”,而且对“沉睡于人类身上仍然难以解释的自然法则和力量”,如招魂术、透视术、心灵感应等进行研究。(126)1902年,施泰纳被任命为德国神智学学会秘书长,他致力于将自然科学的成就同与现代兼容的真正的灵性觉醒结合起来。(127)
施泰纳坚持认为,神智学能以与自然科学同样的可靠性识别出“高等世界”。但他最终还是摒弃了神智学家更具世界性的进路,在施泰纳看来,他们似乎太过折中,太过专注于要把现存世界宗教的各种因素整合起来。(128)他更为“科学”的进路和个体主义聚焦于个体的启蒙,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相对,所以吸引了许多德国神秘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施泰纳的鼓励下,一群德国神智学家冲破桎梏,组建了德国人智学学会。(129)
人智学试图将灵性和科学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它名义上比神智学更努力地从经验上验证这一学说。比如,施泰纳在指导“光环研究”(aura research)时,用新出现的X光技术和显微镜来进行“实验”。尽管如此,他坚称已经“证明”却无经验证据的神秘学现象,阻止了人智学在科学界被接受。直到1930年代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彼时,第三帝国开始正式支持施泰纳学说中的一些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生物动力学”农业。(130)
人智学至少既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科学学说。施泰纳发表在他自己的神秘学杂志《路西法-灵知》(Lucifer-Gnosis)上的教义和文章,预见了纳粹对亚洲宗教、诺斯替主义及路西法主义的兴趣。比如,1915年,施泰纳去了希特勒在林茨的家乡,发表了名为“基督和路西法与阿里曼(131)的关系”的演讲。施泰纳在演讲中说,“亚洲宗教在演化过程中承载了路西法主义的元素”,“这个元素,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曾拥有过,只是后来被迫抛弃了”。施泰纳的结论是,必须将这些“路西法的遗存”提升为“智慧的力量,用来指导全体人类的进化”。(132)20年之后,纳粹的宗教理论家说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人智学和种族论之间的亲密关系已超过了认识论和宗教的范畴。施泰纳急切地断言欧洲白人的优越性,声称“在精神演化的大循环之中,日耳曼种族走在了最前列”。(133)施泰纳相信“宇宙优生学”,这是他从他的一个追随者那儿借来的话,所谓的宇宙优生学就是种族进化的样本,“不值得参与人类的上升的种族都可以被毁掉”。“人类为了净化自己而抛弃了其中的低级形态,由此使自己上升,”施泰纳认为,“它会和另一个自然王国,即邪恶种族的王国分离,从而越升越高。人类就是这样往上升的。”(134)
人智学家之所以支持优生学,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仰现代科学,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灵性和种族有着内在的联系。“人类的灵魂在不同种族和人种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施泰纳如此说道,“而黑皮肤是由于受到了恶魔的干扰。”(135)照施泰纳的说法,雅利安人和“有色人种”或犹太人通婚与日耳曼的世界使命是相冲突的,所谓的世界使命就是倡导积极的生物和精神的进化。所以,施泰纳和胡伯-施莱登、哈特曼都属于种族主义者、反犹的圭多·冯·李斯特社团也就不足为奇了。(136)事实上,对许多人智学家而言,“犹太身份是精神进步的对立面,是现代堕落的缩影”。(137)
施泰纳自己对犹太人的态度比较复杂,照彼得·施陶登迈耶的说法,“既草率地接纳了反犹偏见,又公开谴责有组织的反犹主义太过猖獗,还弄出了反犹主题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详尽的宇宙进化种族理论”。(138)不过,施泰纳关于犹太生活在现代世界不具有合法性的深奥教义,再加上“他把犹太人描绘成一个独特的种族群体”,这就给“非灭绝性的反犹主义提供了基本前提,这是纳粹主义崛起之前反犹思想的主要模式”。(139)
神智学和人智学影响了广大的奥地利和德国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倾向的人,但它们与种族主义的密切关系或其潜在灭绝性的种族与空间概念,也是不争的事实。(140)神智学和人智学与20世纪初出现的许多神秘学说一样,其诱惑力正是因为它们耗费诸多精力想要“找到一种新的综合方式……将他们所说的知识[Wissen]和信仰[Glaube]综合起来”,提倡荒诞不经的边缘科学种族理论,对人类的历史和未来持末世论观点。尽管这些努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并没有大获成功,却启发了一系列有关种族和空间的理论,“这些后来被民族社会主义收为己用了”。(141)
雅利安智慧学
神智学和人智学或许为更广义的超自然想象提供了信息,这使得德国人受纳粹主义的影响。不过,正是由圭多·冯·李斯特和兰茨·冯·利本费尔斯发展起来的这两者的姊妹学说——雅利安智慧学直接影响了第三帝国。1848年,圭多·冯·李斯特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维也纳家庭,他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倒是对19世纪中叶复兴的异教和民间传说相当感兴趣。1870年代至1880年代,李斯特对日耳曼史前史的业余研究使之相信存在一种古老的前基督教时期的异端宗教和奥丁崇拜者(沃坦人(142))的卢恩文字。他的这种古代异端宗教称为“阿尔玛恩”(Armanen),该词源自塔西佗在其古日耳曼部落史里提到的“赫尔米诺人”(143)。(144)
在胡伯-施莱登和施泰纳的推动下,奥-德神智学已摆托了许多普世主义的伪装。李斯特将他们对种族、帝国和反犹主义的强调推向了(不合)逻辑的极端,“把神智学所推崇的往昔理想盛世和种族演化的宇宙图景拿为己用,以此来支撑他基于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设想出来的新的社会秩序”。(145)李斯特认为,由于和非雅利安人的种族混种繁育,“阿尔玛恩”文明已被削弱,只有严格遵守优生学的选择性繁育计划,才能复苏这个文明。(146)
和施泰纳一样,李斯特也自认为是个严肃的(边缘)科学家,出版了20多部“性学”、种族和精神“卫生”以及日耳曼卢恩文字方面的著作,有的书名还很生动,比如《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1893)和《梅菲斯特》(147)(Mephistopheles,1895)。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没有入主流科学界的法眼。另一方面,他的一些作品,比如他广为人知的《卢恩文字的秘密》(Secret of the Runes,1908)一书有助于从边缘科学角度来研究卢恩文字,这种研究在第三帝国时变得流行开来。(148)
继布拉瓦茨基和施泰纳之后,李斯特也设法将基督教、东方宗教和北欧的种族元素整合进一个尊奉北欧神祇巴德尔、耶稣、佛陀、奥西里斯和摩西的新异教的大杂烩中,但在李斯特的异教里清一色都是雅利安神祇。(149)在建构日耳曼宗教的过程中,李斯特甚至还设立了北欧的昼夜平分点和瓦尔普吉斯庆祝仪式,带领他的追随者穿过古老的“阿尔玛恩人”岩穴,探索维也纳城底下名为“奥斯塔拉”的圣地。(150)李斯特还在其中纳入了共济会骑士团、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传统中的元素。
1911年,李斯特创建了他自己的“阿尔玛恩骑士团”。当然,李斯特的阿尔玛恩哲学里的泛德意志种族主义和灭绝犹太人的反犹主义同布拉瓦茨基的最初意图是不相容的,从某些层面来看也和施泰纳的最初意图不符。不过,这也证明了这些密切相关的学说都具有延展性和兼容并蓄的特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许多顶尖的奥-德神智学家,如奥地利神智学家(哈特曼)和维也纳神智学会的整个分会,都纷纷加入了穷凶极恶的种族主义和反犹的李斯特学会。(151)
李斯特年轻的同代人约尔格·兰茨·冯·利本费尔斯将李斯特的阿尔玛恩主义阐释成了羽翼丰满的神秘学说,称之为雅利安智慧学。兰茨在《神智动物学或索多玛人猿科学和上帝电子》(The Theozoology or the Science of the Sodom’s Apelings and the God’s Electrons)一书以及《奥斯塔拉》杂志中,为第三帝国后来采取的许多优生政策绘制了蓝图。其中包括禁止跨种族通婚、选择性生育和一夫多妻制,并提倡对低等种族(从智力缺陷、身体缺陷到犹太人,都属于此范围)进行绝育,将其消灭。(152)
兰茨的生物学观点充满了概念上的矛盾和不科学的推论,这在世纪末神秘主义和后来的纳粹种族观中很典型。(153)有人要他解释他把“低等的”犹太大众和卡尔·克劳斯(154)、海因里希·海涅以及巴鲁赫·斯宾诺莎这样的犹太天才之间区分开来的科学依据在哪里,兰茨的回答是:“无论谁看见卡尔·克劳斯,都会马上承认他的相貌既不属于蒙古人种,也不属于地中海类型……他头发为深褐色(年轻时肯定是浅褐色),头骨匀称端正,为矩形,五官如雕刻出来的一般,这是赫洛伊德人种(heroid)[纯雅利安人]的特征。”(155)
兰茨信徒的观点也很牵强。他们声称人类“是天使和野兽(不该出现)混合的产物。每个人身上都有少量天使的成分和大量野兽的成分”。一个种族身上的“天使”成分越多,就越接近北欧的种族。这种逻辑认为:“挪威山村的居民或许有高达百分之一的天使成分。”(156)兰茨的助手甚至相信“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气味”,这个论点后来被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这样的纳粹弄得神乎其神(“好鼻子始终能嗅出犹太人的味道”)。(157)
兰茨还宣扬一种包含诺斯替、异教以及东方风格的融合性宗教,这预示了纳粹对宗教的态度。(158)作为对李斯特的“阿尔玛恩”的效仿,1900年,兰茨创建了自己的新圣殿骑士团(Ordo Novo Templi)。他还买下了一座城堡,即沃芬斯坦堡,把他的新骑士团的宗教中心设在那里(这和希姆莱30年后买下威维尔斯堡很像)。1904年,他在那里挂起了纳粹万字旗,庆祝异教的冬至日。(159)
最后,兰茨还深深扎进了对东亚和南亚符号的力量的研究,认为它们和欧洲的雅利安-日耳曼卢恩符文具有相同的根源。他赞同印度教的转世和业的概念,也赞成基督教的天堂和地狱的概念,还涉猎过卡巴拉(奇怪的是,在激进的反犹人士中这是个常见的主题)。(160)甚至他大量使用的指代低等人种的Tschandals一词(后来被早期纳粹党采用)也是借用自印度教的《摩奴法典》,“摩奴”一词源自“梵语chandala(Tschandale),指贱民的最低种姓”。(161)
如果我们一定要把李斯特和兰茨那些怪异的想法提炼成几个基本原则的话,那超人种族可能不得不提,超人种族的雅利安黄金时代早已被低等种族“怀有敌意的异质文化所取代”。这种古老的日耳曼宗教可以通过“形式隐晦的知识(比如卢恩符文、神话和传统)”来恢复,但这样的卢恩符文和传统“最终只能由其灵性的继承人,即现代的宗派分子来解读”。(162)这种混合了宗教千禧年主义和优生学的大杂烩,很快就和“种族卫生”及“种族繁育”(Rassenzucht)这两个流行的边缘科学交汇在一起,后者在阿尔弗雷德·普吕茨之类的主流生物学家中间很流行。(163)
因此,雅利安智慧学和其他我们考察过的神秘学学说具有一致性。无论是神智学者,还是人智学者,都在全神贯注地思考如何使雅利安人(“第六根种族”)起死回生。两者都相信,至少在它们的奥-德各迭代中,雅利安人在精神上和生物学上都要优于犹太人、亚洲人和非洲人。(164)和神智学者及人智学者一样,雅利安智慧学家也和同一拨占星师和招魂师一起做实验,给同样的杂志供稿,并在维也纳、慕尼黑和柏林的同一圈子里活动。(165)正如胡伯-施莱登的《斯芬克斯》(Sphinx)杂志和施泰纳的《路西法-灵知》杂志会刊登李斯特和兰茨的文章,德国著名的占星术杂志《占星术评论》(Astrologische Rundschau)也由雅利安智慧学家鲁道夫·冯·塞博滕道夫来编辑。(166)
相比人智学家和神智学家,雅利安智慧学家更能将重要的种族论政治家和未来的纳粹党人吸引到他们的运动中来。希特勒在煽动人心方面的榜样——维也纳民粹派市长卡尔·吕格就是圭多·冯·李斯特学会的会员。(167)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意识形态和精神事务上的导师、党卫军档案馆馆长卡尔·马利亚·威利古特本身也是雅利安智慧学家,出版了有关阿尔玛恩人(赫尔米诺人)宗教和卢恩符文学领域的大量著作。原纳粹修黎社的共同创始人塞博滕道夫也是阿尔玛恩的后续组织日耳曼骑士团的领导人。正如兰茨所说,即便希特勒从来没读过《奥斯塔拉》杂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渗透进维也纳咖啡馆和慕尼黑啤酒馆的那些神秘学学说显然也有助于塑造纳粹的超自然想象。(168)
三、边缘科学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学院派人士“遇到了大量不遵循既定科学探究规则的理论”。(169)一些开花结果的“‘类似于宗教’的自然科学”,即当时有些人所称的“边缘科学”(Grenzwissenschaft),处于主流科学的边缘地带,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170)
一方面,边缘科学研究的是人类感知边缘不可见的力量、特点或现象。其中包括占星术、笔迹学、性格学(在德国属于颅相学的一种,通常和占星术相结合)、手相学(“手的研读”)、通灵学和射线探测术。边缘科学也构成了受到学院派怀疑的边缘学科,它们看起来解释了如何操控莫测高深的或超自然的力量,这是主流科学所没法理解的。突出的例子包括超心理学、生命改良(171)、心灵感应、生物动力学农业和“冰世界理论”。
将所有这些“复魅科学”(reenchanted sciences)结合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超常是科学探究和力量的合法客体。(172)著名的边缘科学家恩斯特·伊斯伯纳-哈尔达纳写道,占星术、笔迹学、性格学和手相学与其他任何科学一样“严肃、精确、精深”,而且“对经济学和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照伊斯伯纳-哈尔达纳的说法,边缘科学“避开了任何一种神秘主义,和所有的灵视绝缘;如今,它们不再属于玄学(不为人知的理论)”,而是属于客观科学。(173)
阐释自然世界的超心理学实验和边缘科学研究并非中欧德语地区所独有。顶尖的抽象画家之一瓦西里·康定斯基就是灵性论的坚定支持者。法国和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如夏尔·里歇和威廉·詹姆斯,也都对超常现象进行过试验。(174)
然而,和德国形成对照的是,很少有欧洲人“像德国浪漫主义者那样对牛顿于新现代科学的贡献感到绝望”,也没有几个欧洲人觉得“人类如今注定只能生活在一片死寂的粒子宇宙之中,没有树妖(175),也不存在精神意义”。(176)许多德国科学家对现代物理学和化学的兴起倍感痛心,认为这些学科将“五彩斑斓、有品质、有自发性”的世界转变成了一个“冰冷的、无品质可言的非人领域……物质的粒子在其中犹如牵线木偶一般按照数学的计算定律舞动”。(177)
数百万德国人并没有接受主流的自然科学,而是转投了超心理学、占星术、“超验物理学”以及“冰世界理论”这些边缘科学。(178)约翰·雷迪克推测,对“复魅”科学广泛产生兴趣乃是1870年以前德国国家支离破碎的产物,也是渴望种族和领土“保持完整性和综合性,而不满足于日常现实”的产物。(179)科琳娜·特莱特尔同样认为,德国对超心理学的特别看重,也许是对1848年革命不成功之后德国各州丧失政治机构的一种反应。(180)不管是什么原因,若是不了解边缘科学学说在奥-德超自然想象中的深度和广度,那就无法理解第三帝国对政治和社会、种族或空间的态度。
超心理学和占星术
超心理学有可能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的最“合理”,而且最包罗万象的“边缘科学”。早期的超心理学具有决定性的批判优势,心理学家马克斯·德索伊尔和犯罪学家阿尔伯特·赫尔维希在审视了“欺骗和怀疑的心理学”后就是这么说的。最慷慨大度、极具批评精神的超心理学家们努力解释了秘术科学在德国的盛行,正如十年后马克斯·韦伯所做的那样,用的是社会心理学术语,他们提到无论是传统宗教还是科学唯物主义,都不足以解答紧迫的本体论问题。
但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超心理学家的目的并不真心诚意地“理解”神秘主义,当然也不是为了证明神秘现象的存在。他们是为了揭露灵媒、巫师以及其他习秘术者都是骗子。(181)赫尔维希认为,神秘主义是一种“心灵的传染病”,缺乏一定的科学知识的人易受感染:“经验日复一日地表明,只要涉及神秘学问题,许多人就不再能够静下心来进行批判性思考。当有人发现有些学院派人士或许在许多科学领域颇有建树,可此时却完全丧失了逻辑和理性能力,这一点着实令人悲哀”。(182)
批判性没这么强烈的一类超心理学家则声称巫师、透视者和占星师具有同等的科学合法性,试图证实这些人的说法。德国在该领域最著名的超心理学家是卡尔·杜·普雷尔和阿尔伯特·施伦克-诺青格。受布拉瓦茨基的启发,杜·普雷尔用生物学、唯心论和占星术来解释人类生物性和意识的演化过程。(183)1884年,杜·普雷尔加入了德国神智学学会,和胡伯-施莱登合作创建了心理学学会以支持他的边缘科学研究。他还在神智学杂志《斯芬克斯》上发表了自己的许多“成果”。(184)
施伦克-诺青格在慕尼黑当医生和催眠师,是杜·普雷尔的门生,1880年代加入了心理学学会,将其导师的“超验心理学”推得甚至更远。施伦克-诺青格着重研究“灵魂的夜生活”,这表现出了一种明显受神秘主义启发,同注重假设的自然科学分道扬镳的特征,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神智学圈子里广受欢迎。(185)
事实上,奥-德秘术师热情地接纳了施伦克-诺青格“未经批判的”超心理学。正如弗朗茨·哈特曼所注意到的,超心理学“恢复了启蒙时代遭压制的人类体验的整个领域。这是潜意识的领域……对科学家和哲学家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他们不能把这留给巫师。”(186)体现作为新学科的边缘科学的资质的是胡伯-施莱登的《斯芬克斯》,该杂志“并不以迎合受过专门教育的读者而自诩”,“会刊登一大堆关于通灵、占星术、玫瑰十字会、神智学、射线、颅相学和瑜伽方面的文章和……感官论者的……报告”。(187)
超心理学的科学基础是可疑的,主流心理学家并没有忘记这一点。批评人士认为,超心理学家更喜欢在非中立的环境里进行试验,比如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或使用暗红色的光,以干扰观测者,使之无法进行准确的观测。(188)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指出过超心理学信仰在方法论和意识形态出处上的问题。弗洛伊德认为,从方法论上看,相信存在超常现象乃是潜意识冲动和情结的一种功能,很容易被灵媒和超心理学操纵,而他们自己往往也对虚幻的“神秘情结”信以为真。(189)
此外,作为一名犹太自由主义者和科学唯物论者,弗洛伊德并不相信神秘论的根源是寻求培养“海洋情感”、“声称要[实现]个体内在和谐”的“印度东方主义”。在东方神秘主义的浸染下,超心理学对已经怀疑科学的人提供了“虚假的帮助”。弗洛伊德还说,超心理学可以用于强化人们对犹太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看法,认为犹太“种族在中世纪时期对所有的传染病负有责任,如今他们则是奥匈帝国解体和德国战败的罪魁祸首”。(190)弗洛伊德在这儿先行一步,预见到了神秘主义和超心理学可能会为那些已经倾向于寻找种族替罪羊的人提供一种危险的万灵药。
超心理学家指责弗洛伊德和其他批评者在分析神秘现象时也不够“科学”。边缘科学家认为,任何相信通灵都能通过诡计和欺骗来影响许多人的人,其本身就有精神疾病。(191)卡尔·荣格也赞同这些论点。(192)和弗洛伊德不同,荣格“被他那个时代中欧东方主义者的雅利安主义所包裹”,断言“雅利安人的潜意识比犹太人的潜意识具有更大的潜力;这是一种还没有完全和野蛮残忍脱钩的青年时代的优势,也是劣势”。(193)
受到荣格等“主流”心理学家支持的超心理学家继续声称他们的方法具有科学性,指责他们的对手患有精神疾病,坑蒙拐骗。这种在神秘学和边缘科学内部以及神秘论者和主流自然科学家之间互相指责的模式,是那个时代为科学合法性而斗争的特有现象,预示着纳粹和第三帝国的主流科学家之间的关系会日趋紧张。(194)
正如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1895)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面对不具批判性的或完全无知的同辈,即便是现代社会最有智慧、最具怀疑性的个体也会屈服于别人的建议。这种现象对于受“专家”影响的人群尤其如是,而此处的“专家”就是指受过训练的灵媒或像希特勒这样有魅惑性的政治家。(195)
勒庞的理论被批评人士拿来解释神秘论信仰为何会扩散开来,无论是在施伦克-诺青格家的客厅里进行假定性“实验”的某个小团体,还是大众媒体、杂志和表演,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批评人士认为,只要研究超心理学家的“神经质、好斗、肤浅、健忘、轻信和有号召力的”头脑,就能对那些想要提倡科学神秘论的人的心理洞若观火。(196)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的那样,希特勒似乎研究了勒庞的理论和超心理学,以此作为操控公众的手段。(197)
除了超心理学之外,占星术也是德国和奥地利极其流行的边缘科学。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占星师“解读”星星,画出天宫图。天宫图代表的是一种对“天体现象的客观陈述”,是以“地心的星体方位‘地图’”为基础的,包括“星体中的太阳和月亮,以及它们和黄道带的关系”。天宫图可适用于许多不同的事项,不仅可应用于人和动物,也可用于地震观测和船舶下水。一旦星体的方位确定,便可基于星体彼此在黄道带上的角度来进行推算。(198)
19世纪上半叶,德国人对占星术的兴趣也许并不比其他欧洲人多。但正如埃里克·豪所指出的,现代德国占星术的复兴和上述超自然及边缘科学思想的总体复苏正好同时发生。(199)“德国人对理科持怀疑态度,发现它们对生命怀有敌意”,发现“占星术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可以用直觉的方法进行技术上的分析。‘既具有逻辑上的严谨,又拥有情感上的温度’的占星师还提供了‘针对有精神需求的个体的特定服务’。”(200)
占星术是一种超自然的解决方法,事实上几乎将所有的神秘论和边缘科学从业者都联合了起来。胡伯-施莱登鼓励他在《斯芬克斯》的门生雨果·沃拉特创立了一家神智学出版社,以推广占星术。演员卡尔·布兰德勒-普拉希特受到一场降神会的启发,1905年开始出版德国标杆性的占星术杂志《占星术评论》。由鲁道夫·施泰纳和新的德国占星师宇宙学会[其官方杂志为《神秘学文摘》(Zentralblatt für Okkultismus)]共同资助,布兰德勒-普拉希特在德国的神智学和人智学圈子内找到了一批现成的读者。(201)无论是李斯特还是兰茨,都从事占星术。塞博滕道夫也是,他后来担任了《占星术评论》的编辑,还将六期杂志捐赠给了沃拉特的“占星术图书馆”。(202)
虽然几乎所有神秘论和边缘科学思想家都在拥抱占星术,但这并不意味他们会对该学说之中的具体细微观点都表示赞同。占星师们使劲地争相证明究竟谁的方法更“科学”,谁的更讲究“直觉”——后者被人与要求不那么严格的神秘论学说联系在一起,遭人轻视。(203)这样的区分与其说是“非理性”的神秘论者和“理性”的科学家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边缘科学圈内“科学、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冲突。(204)深深植根于战后德国的超自然想象的占星术和超心理学,只是在两次大战期间才流行开来,并且产生了影响。(205)
射线探测、生命改良和“冰世界理论”
超心理学和占星术为神秘现象提供了许多见解——思维是可以扩展到物质之上的,存在可以操控其他人的力量,预测未来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与之密切相关的边缘科学领域,如射线探测术(“探测术”)和宇宙生物学这一占星术的分支学科,却许诺能带来更广泛,更具体的生物和环境的好处。因为有些知名的探测师和宇宙生物学家在物理学及工程学领域都有高级学位,许多对流行的占星术持怀疑态度的德国人也都接受了射线探测术,视之为“科学”。甚至一些医学专业人士,通常是那些倾向于顺势疗法的医生,也相信射线探测术可以提供一种方法来净化躯体、清理环境,使之不受不明物质的影响,而现代科学却做不到这一点。(206)
使用探测棒来确定水和重金属的方位,一直是中世纪时期欧洲民间信仰的固有部分。这种民间传统到了近代早期就和神秘论信仰结合了起来,后者认为可以在某些地形(指的是“地脉”)确定神秘“能量”的方位,将不可见的“射线”压制在地下。(207)20世纪早期,探测术也被归入“地相术”和“射线探测术”这些常规的边缘学科,其操作方式多种多样,但通常都会用到摆锤,摆锤是个“小圆木柱……用一根细细的短绳吊着”。(208)
诸如有名的古斯塔夫·弗莱黑尔·冯·波尔之类的探测师,声称会用摆锤或更为传统的探测棒来定位地里的射线和其他致病流(Reizstreifen),前者带有不可见的能量,后者会威胁人类的健康。(209)射线探测术,明面上能够以传统物理学和生物学都无法做到的方式来定位和处理有害的射线(因此,属于“宇宙生物学”这一跨学科领域)。(210)与地相术密切相关的领域有种族-秘术师,如威廉·托伊特,他们“假定有关原始能量的史前知识”证明了“原始人(Urgermans)的优越性”。(211)有些探测师精力主要放在定位射线和贵金属上面。另一些则声称他们可以收集有关物品甚至是人际关系的秘密真相。(212)
对于探测师可以找到导致癌症和疾病的不健康能量的笃信,与自然疗法运动水乳交融,后者就内嵌在“生命改良”之中。“中产阶级试图减轻现代生活的弊病”,生命改良拥抱的是“各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如草药和天然医学、素食主义、天体主义和自给自足的乡村社区”。(213)许多种族神秘论者信奉“自然”(有机)食物和素食、磁疗和自然疗法,后来,像希特勒、赫斯、希姆莱以及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等纳粹领导人也都接受了这些做法。(214)生命改良受到了人智学学者特别热情的推广,他们主张“对人了解得更透彻;通过自然生活来实现健康;在血液、土壤和宇宙之间保持和谐;生命改良是国家目标;知识和生活,生存的法则”。(215)
生命改良的原则反过来又启发了施泰纳在战后发展出了“生物动力农业”(biodynamische wirtschaftweise,简称BDW),其理论的依据是恢复土地和宇宙之间近乎神秘的关系,“在这层关系中,土地被视为一个具有同情心和吸引力的磁性有机体,可能会因为使用人工肥料而受损”。(216)施泰纳的生物动力农业后来成了第三帝国时期最突出,使用最广泛的边缘科学之一。(217)
射线探测术、生命改良、自然疗法强调的是种族和精神“卫生”之间、心灵健康和身体健康之间的整体关系。这两个密切相关的边缘科学对日益强调临床治疗的医学重新赋予了特性,临床医学针对的是特定的细菌、病原体和疾病,这同整个人或“有机体”是对立的。他们还呼吁采取超验的世界观,以此对疾病进行更直觉、更全面的理解,这和关注个体疾病致病源的唯物主义方法是背道而驰的。(218)
边缘科学在摒弃主流医学的同时,偏爱采用“各种并不昂贵也不具有侵害性的技术(如透视术、恒星运行摆锤、相面术、笔迹学、虹膜学、降神术和占星术)来对疾病进行直观而且更为全面的理解”。传统医生对做长期预测非常谨慎,而射线探测师、治病术士和生命改良师却“用直觉的方法来做这样的预测”,并“决定合适的治疗时机”。(219)
当然,顺势疗法和回归自然运动(Wandervog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数十年的欧洲很流行。(220)探测术和生命改良激发了对“复魅科学”和身心整体论的广泛渴望,后者在德国中产阶级中颇为流行。(221)不过,如果说生命改良包含了“明显的自由主义和左翼”元素,那么至少在德国和奥地利,“它们和种族运动有诸多重合之处”。(222)正如奥-德版的神智学比法国或英美版的神智学更具有鲜明的种族主义和雅利安中心论色彩,奥-德版的自然疗法和边缘医学方面的变体也是如此,这些变体从人智学和雅利安智慧学中汲取养料,对种族和优生学更为关注。(223)
人智学强调的是通过适当地开垦土地和培育同宇宙相关的精神,雅利安种族就能复兴。(224)人智学学者也常常认为“种族混杂带来精神上的不和谐”,只有“种族人种学才能洞察表象背后的‘真正的宇宙精神’”。(225)人智学学者和雅利安智慧学学者由此相信“有色人种”或者犹太人与雅利安人之间的婚嫁,会和德国的世界使命相冲突。(226)
在帮助构建第三帝国以信仰为基础的优生学实践的过程中,这种“复魅科学”绝非无害。(227)事实上,生命改良的领导者和回归自然运动的领导者与提倡优生学的种族-秘术群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力挺乌托邦“花园城市”运动的人寻求在现代城市中心创建健康的“绿色地带”,但他们也是种族-秘术师,如特奥多尔·弗里奇、海因里希·普多尔和菲利普·施陶夫。(228)
弗里奇的同事、种族-秘术作家威利巴尔德·亨切尔也推动了一种激进的回归自然的优生主义意识形态。亨切尔预见到了第三帝国,设想了一个由纯雅利安农夫践行北欧古老宗教的庞大殖民地。他在战前参加的由“诺恩(229)小组”(Norn-lodges)组建的“修黎定居点”计划,从未实现。不过,他们确实启发了战后的阿塔曼纳(230)运动和纳粹的种族重新安置和人种清洗政策,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瓦尔特·达雷都是该运动的成员。(231)
威廉时代后期的流行文化充斥着由生物学和巫术相结合创造超人的想法。(232)保罗·威格纳的电影《魔像》(Golem,1915和1920)和汉斯·海因茨·尤尔斯的小说《阿尔劳娜》(Alraune,1911)都是边缘科学思维的产物,体现了这种将科学和超自然随意混合的现象。(233)1914年之前,这种受超自然影响的生物学研究路数还不是太可怕,“还能提供一系列政治解决措施,处理现代性和怀旧、机制和整体性、科学和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234)
但1918年之后,在一个因为战争和危机而变得激进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种受超自然影响的生物学研究路数帮忙将欧洲流行的有选择性的优生学实践方式转变成了纳粹德国野心勃勃、荒谬绝伦的人体实验和种族灭绝计划。
对影响纳粹主义的边缘科学学说进行研究,如果不提“冰河宇宙进化论”(Glacial Cosmogony)或“冰世界理论”,就算不上完整。由奥地利科学家、哲学家汉斯·霍尔比格发明的“冰世界理论”受到他自己做的一个梦的启发,在这个梦中,霍尔比格发现自己漂浮在太空中,看到一个巨大的摆锤来回晃悠,那摆锤越变越长,最后以断裂收场。醒来后,霍尔比格声称自己凭直觉知道了海王星和太阳之间的距离达到现有的三倍时,太阳的引力就停止对其起作用,而且绝大多数物理宇宙都能通过“冰与火这些彼此对立的原始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做出解释。(235)
就连基本的科学素养都欠缺的霍尔比格找来了业余天文学家菲利普·佛特,并于1912年与之合作出版了他们的“发现”,也就是《冰河宇宙进化论》。(236)他们的这部作品假定一颗充满水的小恒星和一颗比它大很多的恒星相撞,发生爆炸,产生的结冰的碎片创造出了多个太阳系,包括我们所在的太阳系,已知宇宙的大部分就是这么来的。地球引力、行星的自转以及其他星际现象,都能通过冰块生成的原始卫星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地球的地质史也是如此,因为在史前时期,由冰块构成的多个月亮撞击地球,才产生了洪水、冰河时期以及地壳的不同层次。就连人和动物的生物学都能通过“冰世界理论”来解释,即含有“神圣精子”的流星撞击之后人类才被创造了出来。(237)
霍尔比格及其支持者声称,“冰世界理论”是一场“科学革命”,它为基于“创造性直觉”的崭新的“宇宙文化史”、“不可见之物的天文学”奠定了基础。(238)尽管如此荒诞和一概而论,但霍尔比格“包罗万象的天球理论”承诺要解决“创世之初和世界崩塌之间的宇宙之谜”。从“太阳和物种的起源”到“墨西拿的地震”、印加宗教、北欧神话,没有它解决不了的。(239)
作为“冰世界理论”的超级“领航员”,霍尔比格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逻辑、主题和体系,用自己的理论反驳主流科学的任何论点。(240)霍尔比格提供了所有必需的线索,让读者确信他们所看见的才是真正的“科学”,他的学说“至少对广大公众来说,可以产生货真价实的感觉,使注重客观和理性的‘严肃的’科学作品与夸大其辞的儿戏之作区分开来”。(241)因此,“冰世界理论”是一门典型的边缘科学,它自豪地将奇思异想和现实混在一起,讨好了渴望灵性的普通民众,却也激怒了科学家。(242)
确实,很少有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或地质学家愿意为霍尔比格的理论背书。照天文学家埃德蒙德·魏斯的说法,霍尔比格的直觉方法同样可以拿来断言宇宙是由橄榄油构成的。和大多数边缘科学家一样,霍尔比格对批评意见充耳不闻,还指责对方头脑狭隘,对他的观点缺乏“信任”。霍尔比格说,没有公式或数字能证明“冰世界理论”,因为他的理论是不断变化的、活跃的,是一种“崭新的福音主义”和“放眼全球的拯救观”(erloesendes Weltbild)。(243)因此,他反而专注于说服普通民众相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希望这可以让主流科学更认真地对待他的观点。他公开讲学数百场,制作了冰世界电影和广播节目,出版冰世界小说和杂志。(244)
1920年代,一些业余科学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手组建了宇宙科技学会(Kosmotechnische Gesellschaft)和霍尔比格研究所,围绕霍尔比格和他的教学形成了近乎邪教的崇拜。(245)他的理论还吸引了雅利安智慧学和日耳曼异教徒,如张伯伦、李斯特、兰茨·冯·利本费尔斯,他们从“冰世界理论”上发现了他们“奇异的宇宙学和壮观的世界观”的“科学”证明。由此,这种原日耳曼学说替代了“犹太”物理学和“无灵魂可言的”自然科学,而大洪水、末日之战以及英勇的雅利安埃达文明似乎都被证实了。(246)
“冰世界理论”的广受欢迎,成为20世纪最初30年神秘学和边缘科学广泛复兴的标志。诸如“冰世界理论”、超心理学、占星术等现象既没有落伍,也没有边缘化。它们是“科学秘术论”受欢迎的表现,这类理论想在科学殿堂里和更广的民众中谋求合法性。(247)尽管遭到国家官员、自由主义者甚至保守的宗教团体的攻击,神秘学和边缘科学仍越来越受欢迎,“不仅成了宗教新贵,也成了科学新贵”。(248)在制造一门“灵魂科学”,一门超越了科学唯物主义和传统宗教的“复魅科学”的过程中,边缘科学使得德国人有机会来挑战这两者的权威。
***
希特勒也许读过《奥斯塔拉》杂志。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学艺术的学生,他也可能拜访过兰茨·冯·利本费尔斯。但即便没见过面,“希特勒和雅利安智慧学圈子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联系”也相当重要。(249)因为李斯特和兰茨很难说成是边缘人物。他们的想法和目标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同时代人有许多共同点。从瓦格纳、拉加德、朗贝恩到胡伯-施莱登、哈特曼、施泰纳,从普雷尔和施伦克-诺青格到舒勒和霍尔比格,这些人应该被视为一个集体、广义上的超自然想象的先驱,他们的想象不仅被数百万德国人接受,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纳粹党加以利用。(250)
本章的第二个论点是,奥-德超自然想象传播了一种秘术和边缘科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既表现为普世的宇宙观,又表现为整体性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和数百万德国人联合了起来,因为他们“担心纯唯物主义的抽象科学会导致文化没落”。(251)确实,本章考察的大多数学说都试图挑战启蒙时代科学对知识的垄断以及犹太-基督教传统对灵性的垄断。(252)
许多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主流科学家都对这些无法证实的边缘科学学说的扩散感到不安。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有些人发现超自然思维会鼓励种族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倾向,尤其是当它们和科学主张不加区分地等同起来的时候。(253)
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超自然和超感官在德国和奥地利知识精英中很有市场”。(254)与数以千计的占星师、超心理学家、探测师、冰世界理论家、神智学家和人智学家相呼应的是,奥-德种族理论界的领袖也创造了一种未来观,这种未来观超越了传统的左派和右派、宗教和科学、种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分,硬生生地将威廉时代后期和魏玛的社会、文化、政治一分为二。
科琳娜·特莱特尔的观察相当准确,“纳粹主义得以演化的种族论环境”是相当复杂的。数百万种族论运动的成员,无论是秘术师、异教徒还是边缘科学家,都坚决不赞同用“适当的手段”来影响政治变革。但所有的种族论思想家又都赞同德国需要复兴。(255)德国复兴规划中注入了超自然学说,垄断这一规划的正是纳粹党。
(1)The Month:An Illustrated Magazine of Literature,Science and Art 610(April 1915),p.354.
(2)Mosse,Masses and Man,p.213.
(3)Ostara,奥斯塔拉是古日耳曼的春日女神。——译者
(4)Wilfried Daim,Der Mann der Hitler die Ideen Gab,Vienna:Böhlau,1985,pp.25-7.
(5)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94-8.
(6)Ostara 39(1915);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93-4;Daim,Der Mann,pp.160-75.
(7)Tschandals,这是弗里德里希·尼采从印度种姓制中借用的一个词,指最低等的种族。——译者
(8)欲了解更多有关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更广泛概念的详细信息,参见Uwe Puschner,‘The Notions Völkisch and Nordic’,in Horst Junginger and Andreas Ackerlund,eds,Nordic Ideology Between Religion and Scholarship,Frankfurt:Peter Lang,2013,pp.21-32。
(9)Mosse,Masses and Man,p.69;see also Max Weber,Science as a Vocation,Indianapolis,IN:Bobbs Merrill,1959(1918);Rodney Stark,Discovering God,New York:HarperCollins,2004;James Webb,The Occult Underground,London:Open Court,1974;Thomas Luckmann,The Invisible Religion,New York:Macmillan,1967,pp.44-9;Williamson,Longing,pp.12-18;Geppert and Kössler,eds,Wunder,pp.9-12;Steigmann-Gall,Holy Reich,pp.112-13.
(10)See ‘Introduction’,in Black and Kurlander,Revisiting,p.9;see also Staudenmaier,‘Esoteric Alternatives in Imperial Germany:Science,Spirit,and the Modern Occult Revival’,in Black and Kurlander,Revisiting;see Treitel,Science;Pasi,‘The Modernity of Occultism’,in Hanegraaff and Pijnenburg,eds,Hermes,pp.62,67-8.
(11)See Williamson,Longing,pp.1-6,294-8;Brigitte Hamann,Hitlers Wien:Lehrjahre eines Diktators,Munich:Piper,1996,pp.7-9,285-323;Ellic Howe,Urania’s Children,London:Kimber,1967,p.4;Thomas Weber,Hitler’s First Wa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255-60;Mosse,Masses and Man,pp.178-80.
(12)Mosse,Masses and Man,p.69.
(13)H.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trans. and ed.),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p.153-4.
(14)同上。
(15)See Weber,Science;Stark,Discovering God;Webb,Occult Underground;Eva Johach,‘Entzauberte Natur? Die Ökonomien des Wunder(n)s im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Zeitalter’,in Geppert and Kössler,eds,Wunder,p.181;Harrington,Reenchanted Science,xx.
(16)See Mosse,Masses and Man;Rupnow et al.,eds,Pseudowissenschaft.正如莫尼卡·布莱克提醒我们的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里,已经看到了传统的新教-天主教忏悔分歧之外的宗教运动蓬勃发展。”Monica Black,‘Groening’,in Black and Kurlander,Revisiting,p.212。
(17)ChristianVoller,‘Wider die “Mode heutiger Archaik”:Konzeptionen von Präsenz und Repräsentation im Mythosdiskurs der Nachkriegszeit’,in Bent Gebert and Uwe Mayer,Zwischen Präsenz und Repräsentation,Göttingen:De Gruyter,2014,pp.226-7.
(18)‘Germany,but where is it? I don’t know how to find such a country’,in James J. Sheehan,‘What is German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the Nation in Ger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3(March 1981),p.1.
(19)http://www.virtualreligion.net/primer/herder.html.
(20)Gugenberger and Schweidlenka,Die Faden,pp.97-9.
(21)Mosse,Nationalization,pp.7-8,14-15,40-3;Bernard 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9:2(2004),pp.255-70.
(22)Darnton,‘Peasants Tell Tales’,in Great Cat Massacre,pp.35-41.
(23)Louis L. Snyder,‘Nationalistic Aspects of the Grimm Brothers’ Fairy Tales’,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2(1951),pp.209-23;Maria Tatar,‘Reading the Grimms’ Children’s Stories and Household Tales’,in Maria Tatar,ed.,The Annotated Brothers Grimm,New York:Norton,2012 pp. xxvii-xxxix.
(24)Gugenberger and Schweidlenka,Die Faden,pp.103-5.
(25)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193.
(26)Mosse,Masses and Man,pp.76-7;see also Hannjost Lixfeld,Folklore and Fascism:The Reich Institute for German Volkskunde,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p.21-2;Woodruff D. Smith,Poli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Culture in Germany,1840-192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62-3;Ellic Howe,Rudolph Freiherr von Sebottendorff,Freiburg:[private publisher],1989,pp.25-7.
(27)Debora Dusse,‘The Edda Myth Between Academic and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s,’ in Junginger and Ackerlund,eds,Nordic Ideology,pp.73-8.
(28)Uwe 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 im wilhelminischen Kaiserreich,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2001,pp.29-51,125-41.
(29)Williamson,Longing,pp.12-18;Luckmann,Invisible Religion,pp.43-4.
(30)Mosse,Masses and Man,pp.199-208.
(31)Treitel,Science,p.217.
(32)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207-52.
(33)Willibald Alexis,Der Werwolf,Berlin:Jahnke,1904(1848);Hermann Löns,Der Wehrwolf,Jena:Diederichs,1910.
(34)K.F. Koppen,Hexen und Hexenprozesse;zur geschichte des aberglaubens und des inquisitorischen prozesses,Leipzig:Wigand,1858;Wilhelm Pressel,Hexen und hexenmeister;oder,Vollständige und getreue schilderung und beurtheilung dex hexenwesens,Stuttgart:Belser,1860;Joseph Hansen,Zauberwahn,Inquisition und Hexenprozess im Mittelalter:und die Entstehung der grossen Hexenverfolgung,Munich:Oldenbourg,1900;Hugo Gering,Über weissagung und zauber im nordischen altertum,Kiel:Lipsius,1902;Paul Ehrenreich,‘Götter und Heilbringer. Eine ethnologische Kritik’,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38:4/5(1 January 1906),pp.536-610;Alfred Lehmann, Aberglaube und Zauberei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an bis in die Gegenwart,Stuttgart:Enke,1908;Hans Kübert,Zauberwahn,die Greuel der Inquisition und Hexenprozesse;dem Ultramontanismus ein Spiegel,kulturhistorischer Vortrag,gehalten am 28. April 1913 im lib. Verein Frei-München,Munich:Nationalverein,1913;Oswald Kurtz,Beiträge zur Erklärung des volkstümlichen Hexenglaubens in Schlesien,Anklam:Pottke,1916;Ernst Maass,‘Hekate und ihre Hexen’,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auf dem Gebiet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50:3/4(1 January 1922),pp.219-31.
(35)Spence,Occult Causes,pp.40-1,72-3.
(36)同上,pp.81-2;Eduard Jacobs,Der Brocken in Geschichte und Sage,Halle:Pfeffer,1879;Michael Zelle,Externsteine,Detmold:Lippischer Heimatbund,2012。
(37)Vehmgerichte,中世纪德国的一种私下审判的秘密刑事法庭。——译者
(38)Andrew McCall,The Medieval Underworld,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72,pp.110-12;Spence,Occult Causes,pp.92-6;P. Wigand,Das Femgericht Westfalens,Hamm:Schulz and Wundermann,1825,2nd ed.,1893;L. Tross,Sammlung merkwurdiger Urkunden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Femgerichte,Hanover,Schultz,1826;F.P. Usener,Die frei- und heimlichen Gerichte Westfalens,Frankfurt:Archiv der freien Stadt Frankfurt,1832;O. Wächter,Femgerichte und Hexenprozesse in Deutschland,Stuttgart:Spemann,1882;T. Lindner,Die Feme,Münster and Paderborn:Ferdinand Schöningh,1888;F. Thudichum,Femgericht und Inquisition,Giessen:J. Ricker,1889;T. Lindner,Der angebliche Ursprung der Femgerichte aus der Inquisition,Münster and Paderborn:Ferdinand Schöningh,1890.
(39)Emil Julius Gumbel,Berthold Jacob,and Ernst Falck,eds,Verräter verfallen der Feme:Opfer,Mörder,Richter 1919-1929:Abschliessende Darstellung. Berlin:Malik-Verlag,1929;Arthur D. Brenner,‘Feme Murder:Paramilitary “Self-Justice” in Weimar Germany’,in Bruce D. Campbell and Arthur D. Brenner,eds,Death Squads in Global Perspective:Murder With Deniabilit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p.57-84
(40)Black,‘Expellees’,p.94;see also Paul Barber,Vampires,Burial,and Death:Folklore and Realit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pp.5-14,90-101;Thomas M. Bohn,‘Vampirismus in Österreich und Preussen:Von der Entdeckung einer Seuche zum Narrativ der Gegenkolonisation’,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56:2(2008),pp.2-5;Raymond McNally and Radu Florescu,In Search of Dracula:A True History of Dracula and Vampire Legends,Greenwich,CT:New York Graphic Society,1972,p.197.
(41)Bohn,‘Vampirismus’,pp.1-2,5-6;J. Striedter,‘Die Erzahlung vom walachischen vojevoden Drakula in der russischen und deutschen überlierferung’,Zeitscrift für Slawische Philologie 29(Heidelberg,1961-2),pp.12-20,32-6,107-20.
(42)Bohn,‘Vampirismus’,p.8.
(43)Mosse,Masses and Man,p.66;Hamann,Hitlers Wien,pp.39-45;Goodrick-Clark,Occult Roots,p.193;August Kubizek,The Young Hitler I Knew (trans. E.V. Anderson),London:Paul Popper and Co.,1954,pp.117,179-83,190-8;Picker,Hitlers Tischgespräche,p.95.
(44)Kurlander,‘Orientalist Roots’,in Cho,Kurlander,and McGetchin,eds,Transcultural Encounters,pp.155-69;Mosse,Masses and Man,pp.69,213,178-80;Williamson,Longing,pp.1-6;Nicholas Goodrick-Clarke,Hitler’s Priestess:Savitri Devi,the Hindu-Aryan Myth and Neo-Nazis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pp.30-5;Nicholas Germana,The Orient of Europe:The Mythical Image of India and Competing Images of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Newcastle:Cambridge Scholars,2009;Sylvia Horsch,‘“Was findest du darinne,das nicht mit der allerstrengsten Vernunft übereinkomme?”:Islam as Natural Theology in Lessing’s Writings and in the Enlightenment’,in Eleoma Joshua and Robert Vilain,eds,Edinburgh German Yearbook 1(2007),pp.45-62;Christian Moser,‘Aneignung,Verpflanzung,Zirkulation:Johann Gottfried Herders Konzeption des interkul-turellen Austauschs’,Edinburgh German Yearbook 1(2007),pp.89-108.
(45)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79-87;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pp.255-70;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Ballantyne,1910,vol.1,pp.264-6,403-36;vol.2,pp.18-25,62-70.
(46)Samuel Koehne,‘Were the National Socialists a Völkisch Party? Paganism,Christianity and the Nazi Christmas’,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7(December 2014),p.763.
(47)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39-43;Kaufmann,Das Dritte Reich,pp.103-4.
(48)Vishwa Adluri and Joydeep Bagchee,The Nay Science:A History of German Ind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31-2,107.
(49)同上。亦可参见Goodrick-Clarke,Hitler’s Priestess,pp.30-5;Germana,Orient of Europe;Horsch,‘“Was findest Du darinne ...”’,in Joshua and Vilain,eds,Edinburgh German Yearbook,pp.45-62;Moser,‘Aneignung’,pp.89-108;Williamson,Longing,pp.294-5;Marchand,German Orientalism,pp.252-91;Kaufmann,Das Dritte Reich,pp.143-4,381-2。
(50)David Motadel,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14,pp.18-28.
(51)See Kurlander,‘Orientalist Roots’,in Cho,Kurlander,and McGetchin,eds,Transcultural Encounters,pp.156-7;Mosse,Masses and Man,pp.69,213,178-80;Williamson,Longing,pp.1-6,294-5;Goodrick-Clarke,Hitler’s Priestess,pp.30-5;Germana,Orient of Europe;Horsch,‘“Was findest Du darinne ...”’,pp.45-62;Moser,‘Aneignung’,pp.45-62.
(52)Myers,‘Imagined India’,p.619;Kaufmann,Das Dritte Reich,pp.145-6.
(53)Adluri and Bagchee,Nay Science,pp.26-7,72-3.
(54)豪尔的学术研究和“其他所有[德国的]印度学家”有些不同,毕竟他“完全是在为宗教、民族主义或人种中心论的需要服务……因为[豪尔]和德国的吉塔学术研究一脉相承……基本上就是混合了Jacobi和Otto的观点”。Adluri and Bagchee,Nay Science,p.277;Kaufmann,Das Dritte Reich,pp.100-1,143-51;Myers,‘Imagined India’,pp.631-62。
(55)Mosse,Masses and Man,pp.213,178-80;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see also Klaus Vondung,‘Von der völkischen Religiosität zur politischen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Kontinuität oder neue Qualität?’,in Puschner and Vollnhals,eds,Bewegung,pp.29-30.
(56)Mosse,Masses and Man,pp.76-7;Hermann Bausinger,‘Nazi Folk Ideology and Folk Research’,in Dow and Lixfeld,eds,Nazification,pp.13-14.
(57)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193.
(58)Manjapra,Age of Entanglement,p.210.
(59)同上,p.210;亦可参见Berman,Enlightenment or Empire;Zantop,Colonial Fantasies;Williamson,Longing,p.4;Motadel,Islam。
(60)Leschnitzer,Magic Background,pp.155-8.
(61)Stern,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62)Junginger and Ackerlund,eds,Nordic Ideology,p.30;see also Repp,Reformers.
(63)See Stern,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pp.5-16.
(64)同上,pp.13-25;Mosse,Masses and Man,pp.199-200,p.13;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Ulrich Sieg,Deutschlands Prophet. Paul de Lagarde und die Ursprünge des modernen Antisemitismus,Munich:Carl Hanser,2007。
(65)Stern,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pp.108-21.
(66)Mosse,Masses and Man,pp.199-200.
(67)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46-51;欲了解“家园”在德国社会和政治想象中的矛盾角色的更多信息,参见Mack Walker,German Home Town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and Celia Applegate,A Nation of Provincial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68)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66-75;Hildegard Chatellier,‘Friedrich Lienhard’,in Uwe Puschner,Walter Schmitz,and Justus H. Ulbricht,eds,Handbuch zur ‘Völkischen Bewegung’ 1871-1918,Munich:K.G. Saur,1996,pp.121-7.
(69)Franz Wegener,Alfred Schuler,der letzte Deutsche katharer,Gladbeck:KFVR,2003,pp.50-73.
(70)Mosse,Masses and Man,p.201;Puschner and Vollnhals,‘Zur Abbildung auf dem Umschlag’,in Puschner and Vollnhals,eds,Bewegung,pp.11-12;‘Germanentum als Überideologie’,in Puschner,ed.,Die völkisch-religiöse Bewegung,pp.266-80;Wegener,Schuler,pp.30-49,74-81;see also Cornelia Essner,Die ‘Nürnberger Gesetze’ oder die Verwaltung des Rassenwahns 1933-1945,Paderborn:Schöningh,2002,pp.37-8.
(71)Stern,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pp.185-202.
(72)Peter S. Fisher,Fantasy and Politics:Visions of the Future in the Weimar Republic,Madison,WI: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3.
(73)See Eric Kurlander,‘Between Völkisch and Universal Visions of Empire:Liberal Imperialism in Mitteleuropa,1890-1918’,in Matthew Fitzpatrick,ed.,Liberal Imperialism in Europe,London:Palgrave,2012,pp.141-66.
(74)Smith,Politics,pp.223-4.
(75)同上,pp.226-8。
(76)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53-5.
(77)Manjapra,Age of Entanglement,p.200.
(78)Smith,Politics,pp.229-32.
(79)Puschner,‘The Notions Völkisch and Nordic’,pp.29-30;Jackson Spielvogel and David Redles,‘Hitler’s Racial Ideology:Content and Occult Sources’,Simon Wiesenthal Center Annual 3(1986),pp.227-46.
(80)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pp.259-61;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92-9.难怪君特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1919年的一本奇怪的小册子,题为《骑士、死亡与魔鬼:英雄理念》(Knights,Death,and the Devil:The Heroic Idea),它将异教、民间传说、神话与生物学上的民族主义及优生学结合在了一起。参见H.K. Günther,Ritter,Tod und Teufel,Munich:J.F. Lehmanns,1920。
(81)Kaufmann,Das Dritte Reich,pp.388-9;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pp.267-8.
(82)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p.268;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00-2.
(83)Klaus Vondung,‘Von der völkischen Religiosität zur politischen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Kontinuität oder neue Qualität?’,in Puschner and Vollnhals,eds,Bewegung,p.29;Kaufmann,Das Dritte Reich,pp.390-1.
(84)Kaufmann,Das Dritte Reich;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pp.268-9.
(85)Howe,Urania’s Children,pp.5-6.
(86)Spence,Occult Causes,pp.59-60.
(87)Treitel,Science,pp.57-8.
(88)同上,p.71。
(89)Webb,Flight from Reason;Owen,Place of Enchantment;Christopher McIntosh,Eliphas Lévi and the French Occult Revival,London:Rider,1972;David Allen Harvey,‘Beyond Enlightenment:Occultism,Politics,and Culture in France from the Old Regime to the Fin-de-Siècle’,The Historian 65:3(March 2003),pp.665-94;John Warne Monroe,Laboratories of Faith:Mesmerism,Spiritism,and Occultism in Modern Fra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90)Treitel,Science,pp.58-9;Hamann,Wien,pp.7-9,285-323;Howe,Urania’s Children,p.4.
(91)Treitel,Science,pp.73-4.
(92)Pasi,‘The Modernity of Occultism’,pp.62-8.
(93)See Stern,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Mosse,Masses and Man,pp.199-200.
(94)Rosicrucianism,为欧洲中世纪秘传教团,以玫瑰和十字为其象征。直至17世纪初,有人在日耳曼地区发表了三份该会的宣言,外人始知该会的存在,但也有人认为该会并不存在。——译者
(95)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59-60.
(96)Armanen,这是1906年奥地利神秘主义学家圭多·冯·李斯特发布的符文。——译者
(97)Howe,Urania’s Children,78-90.
(98)Helena Blavatsky,The Secret Doctrine,New York:Theosophical Society,1888.
(99)Vril,据说这是一种碟形的空间时间转换器。对纳粹统治有影响力的秘密结社中,有一个就叫“维利会”,成员包括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空军元帅戈林、纳粹党秘书长鲍曼等人,企图透过不可知的力量掌握世界,进入新秩序。——译者
(100)同上;Ley,‘Pseudoscience in Naziland’,p.93;see also Julian Strube,Vril. Eine okkulte Urkraft in Theosophie und esoterischem Neonazismus,Paderborn/Munich:Wilhelm Fink,2013,pp.55-74;Alexander Berzin,‘The Berzin Archives:The Nazi Connection with Shambhala and Tibet’,May 2003。
(101)Hyperborean,希腊神话中住在极北之地的人类,他们过得非常快乐,没有疾病老死。——译者
(102)Lemurean,传说中失落的、几乎与亚特兰蒂斯齐名并出现得更早的远古文明。——译者
(103)Blavatksy,Secret Doctrine,pp.150-200,421;Treitel,Science,pp.85-6.
(104)Webb,Flight from Reason.
(105)Hans J. Glowka,Deutsche Okkultgruppen 1875-1937,Munich:Arbeitsgemeinschaft für Religions-und Weltanschauungen,1981,pp.7-15;Treitel,Science,pp.82-3.
(106)Glowka,Okkultgruppen,pp.8-10.
(107)Treitel,Science,pp.85-6.
(108)同上,pp.84-5;Bruce Campbell,Ancient Wisdom Revived:History of the Theosophical Movement,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109)Treitel,Science,p.103.
(110)同上,pp.106-7。
(111)Thule,古代航海家所谓的北极、世界尽头,一个神秘的地方。——译者
(112)同上,p.84。
(113)Engelhardt,‘Nazis of Tibet’,pp.131-4.
(114)Kaufmann,Das Dritte Reich,pp.133-5.
(115)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00-1;Rose,Die Thule-Gesellschaft,pp.37-9;See also Rudolf von Sebottendorff’s history of the Thule Society in Thule-Bote,Munich:Thule-Gesellschaft,1933,p.28.
(116)Südwestrundfunk SWR2 Essay,‘Manuskriptdienst Zivilisation ist Eis. Hanns Hörbigers Welteislehre?’.
(117)Treitel,Science,pp.90-1.
(118)Treitel,Science,pp.90-3。
(119)同上,pp.92-4。
(120)同上,pp.84-9。
(121)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24-6,58-61.
(122)Treitel,Science,pp.94-5;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25-6.
(123)Treitel,Science,pp.95-7.
(124)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27-9,44-5.
(125)Treitel,Science,pp.99-100.
(126)Helmut Zander,‘Esoterische Wissenschaft um 1900. “Pseudowissenschaft” als Produkt ehemals “hochkultureller” Praxis’,in Rupnow et al.,eds,Pseudowissenschaft,pp.78-9.
(127)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26-30.
(128)Zander,‘Esoterische Wissenschaft um 1900’,pp.81-4.
(129)Treitel,Science,pp.99-102;Staudenmaier,Between Occultism and Nazism,pp.24-7.
(130)Zander,‘Esoterische Wissenschaft um 1900’,pp.89-94.
(131)Ahriman,传说中的恶神、暗黑之魔。——译者
(132)See Rudolf Steiner,‘Christ in Relation to Lucifer and Ahriman’,in Kaufmann,Das Dritte Reich,pp.134-5.
(133)Treitel,Science,p.103;Staudenmaier,Between Occultism and Nazism,p.39.
(134)Staudenmaier,‘Race and Redemption:Racial and Ethnic Evolution in Rudolf Steiner’s Anthroposophy’,pp.20-1;Staudenmauer,Between Occultism and Nazism,pp.45-55.
(135)Staudenmaier,Between Occultism and Nazism,pp.164-5.
(136)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24-30,58-61;Treitel,Science,pp.98-9;Helmut Zander,Rudolf Steiner. Die Biografie,Munich:Piper Verlag,2011.
(137)Staudenmaier,Between Occultism and Nazism,pp.264-5.
(138)Peter Staudenmaier,‘Rudolf Steiner and the Jewish Question’,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2005),pp.127-47,128-9.
(139)Staudenmaier,‘Rudolf Steiner’,pp.127-47.
(140)Treitel,Science,pp.84-5.
(141)Black and Kurlander,‘Introduction’,in Revisiting,p.10.
(142)Wotanist,沃坦(Wotan)是北欧种族异教的一种。——译者
(143)公元1世纪左右的日耳曼部族,最初居住在现今欧洲德国北部易北河畔,而后势力逐渐扩张至现今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施瓦本和波希米亚。——译者
(144)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33-40;Mosse,Masses and Man,p.201.
(145)Treitel,Science,pp.104-7.
(146)Mosse,Masses and Man,pp.103-4,207-12;Treitel,Science,pp.74-5;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28-30,59-61.
(147)德国传说中的恶魔,引诱浮士德把灵魂卖给他,以换取物质满足。——译者
(148)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49-50,157-60;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38-9.
(149)Mosse,Masses and Man,p.209;see also Winfried Mogge,‘Wir lieben Balder,den Lichten ...’,in Puschner and Vollnhals,eds,Bewegung,pp.45-52.
(150)Mosse,Masses and Man,pp.103-4,207-12;Treitel,Science,pp.74-5;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28-30,59-61.
(151)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33-48;Treitel,Science,pp.104-6;Mosse,Masses and Man,p.209.
(152)Jörg Lanz von Liebenfels,Die Theozoologie oder die Kunde von den Sodoms-Äfflingen und dem Götter-Elektron,Vienna:Ostara,1905;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80-2,191-3;Daim,Der Mann,pp.23-74;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96-9.
(153)Daim,Der Mann,pp.142-4.
(154)奥地利作家。——译者
(155)同上,pp.144-6。
(156)Ley,‘Pseudoscience in Naziland’,pp.91-2.
(157)同上,pp.91-2;Ernst Hiemer,Der Giftpilz,Nüremberg:Stürmer,1938。
(158)Lanz von Liebenfels,Die Theozoologie oder die Kunde;David Luhrssen,Hammer of the Gods:The Thule Society and the Birth of Nazism,Washington,DC:Potomac,2012,pp.40-1;Daim,Der Mann,pp.23-74;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96-9.
(159)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96-8;Ernst Issberner-Haldane,Mein eigener Weg,Zeulenroda:Bernhard Sporn,1936,p.276.
(160)Kurlander,‘Orientalist Roots’,in Cho,Kurlander,and McGetchin,eds,Transcultural Encounters;Manfred Ach,Hitlers Religion:Pseudoreligiose Element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prachgebrauch,Munich:ARW,1977,pp.8-19;Glowka,Okkultgruppen,pp.14-24;Mosse,Masses and Man,p.209;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90-105;Douglas McGetchin,Indology,Indomania,Orientalism:Ancient India’s Rebirth in Modern Germany,Madison,WI: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9,pp.171-6.
(161)Koehne,‘Were the National Socialists aVölkisch Party?’,pp.778-80.
(162)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77-8.
(163)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73-8;Mosse,Masses and Man,pp.165-71,204-5;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59-60;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pp.35-57.
(164)Treitel,Science,pp.103-4;Kaufmann,Das Dritte Reich,pp.134-8.
(165)Treitel,Science,pp.104-7;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92-4;Essner,Die ‘Nürnberger Gesetze’,p.43;Paul Weindling,Health,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1870-1945,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74.
(166)Treitel,Science,pp.71-4;Howe,Urania’s Children,pp.84-7.
(167)Leo Pammer,Hitlers Vorbilder:Dr. Karl Lueger,pp.3-4,9-11;Bruce F. Pauley,From Prejudice to Persecution:A History of Austrian Anti-Semitism,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2,pp.42-5.
(168)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94-8.
(169)Christina Wessely,Cosmic Ice Theory:Science,Fiction and the Public,1894-1945;http://www.mpiwg-berlin.mpg.de/en/research/projects/deptIII-ChristinaWessely-Welteislehre.
(170)正如Michael Saler提醒我们的,“德国19世纪的科学传统混合了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些对现代神秘主义者的形而上学的思考是挺友好的”,见‘Modernity and Enchantment’,pp.38-51。
(171)Lebensreform,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在德国和瑞士的社会运动,提倡返回自然的生活方式,提倡健康食品、素食主义、天体主义、性解放、替代医学,主张宗教改革,要求戒酒、戒烟、戒药、戒疫苗。——译者
(172)Geppert and Kössler,eds,Wunder,p.26.
(173)Ernst Issberner-Haldane,Mein eigener Weg. Werdegang,Erinnerungen von Reisen und aus der Praxis eines Suchenden,Zeulenroda:Sporn,1936,p.271.
(174)Treitel,Science,pp.8-10,16-18,72-4.
(175)古希腊神话中的树精。——译者
(176)Harrington,Reenchanted Science,p.4;see also Treitel,Science,pp.165-209;Owen,Enchantment;McIntosh,Eliphas Lévi;Harvey,‘Beyond Enlightenment’;Monroe,Laboratories of Faith.
(177)Harrington,Reenchanted Science,p.4;see also Treitel,Science,pp.8-10,16-18,72-4.
(178)Geppert and Kössler,eds,Wunder,p.26;Ley,‘Pseudoscience in Naziland’,pp.90-1.
(179)Harrington,Reenchanted Science,pp.4,19-20.
(180)Treitel,Science,pp.22-5,30-8.
(181)Wolfram,Stepchildren,pp.264-7.
(182)Wolfram,Stepchildren,pp.271-2.
(183)Tomas Kaiser,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Spiritismus:Annäherungen an Leben und Werk des Carl du Prel,Saarbrücken:VDM Verlag,2008,pp.39-54.
(184)Kaiser,Zwischen Philosophie,pp.61-2;Andreas Sommer,‘From Astronomy to Transcendental Darwinism:Carl du Prel(1839-1899)’,Journal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23:1(2009),pp.59-60.
(185)Treitel,Science,pp.43-4.
(186)Treitel,Science,pp.15-16.
(187)The Sphinx merged with Steiner’s occult journal,Lucifer,in 1908;Treitel,Science,pp.53-4.
(188)Wolfram,Science,pp.273-4.
(189)Susanne Michl,‘Gehe hin,dein Glaube hat dir geholfen. Kriegswunder und Heilsversprechen in der Medizin des 20. Jahrhunderts’,in Geppert and Kössler,eds,Wunder,p.216;Wolfram,Science,pp.279-82.
(190)Manjapra,Age of Entanglement,pp.218-19.
(191)Wolfram,Science,pp.282-4.
(192)Michl,‘Gehe hin,dein Glaube hat dir geholfen’,p.217;Ellic Howe,Urania’s Children,pp.2-3.
(193)Manjapra,Age of Entanglement,pp.231-3;Hamann,Wien,pp.7-9,285-323;Howe,Urania’s Children,p.4;Weber,Hitler’s First War,pp.255-60.
(194)Wolfram,Science,pp.263-4.
(195)Jay Gonen,The Roots of Nazi Psychology:Hitler’s Utopian Barbarism,Lexington,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13,p.92.
(196)Wolfram,Science,pp.273-7.
(197)Gonen,Roots,pp.92-3.
(198)Howe,Urania’s Children,pp.8-12.
(199)同上,pp.78-80。
(200)Treitel,Science,p.141;Johach,‘EntzauberteNatur?’,p.181.
(201)Howe,Urania’s Children,pp.78-83.
(202)同上,pp.83-8;Howe,Sebottendorff。
(203)Treitel,Science,pp.138-41.
(204)同上,p.190;Howe,Urania’s Children,pp.84-6。
(205)Howe,Urania’s Children,pp.84-90;Szczesny,‘Die Presse des Okkultismus’,pp.55-6,119-20;Karl Heimsoth,Charakter-Kontsellation,Munich:Barth,1928;Treitel,Science,pp.44-5.
(206)Treitel,Science,p.154.
(207)See Kaufmann,Das Dritte Reich,p.367;Solco Walle Tromp,Psychical Physics: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Dowsing Radiesthesia and Kindred Divining Phenomena. New York:Elsevier,1949;H.H. Kritzinger,Erdstrahlen,Reizstreifen und Wünschelrute:Neue Versuche zur Abwendung krank-machender Einflüsse auf Grund eigener Forschungen volkstümlich dargestellt,Dresden:Talisman,1933;H.H. Kritzinger,Todesstrahlen und Wünschelrute:Beiträge zur Schicksalskunde,Leipzig:Grethlein,1929,pp.65-72;Letter from Sturmbannführer Frenzolf Schmid,21 March 1937. BAB:NS 19/3974,pp.10-11.
(208)See Kaufmann,Das Dritte Reich,pp.363-8;Howe,Nostradamus and the Nazis,p.127.
(209)Treitel,Science,pp.133-4.
(210)Kritzinger,Erdstrahlen,pp.8-22,25-39.
(211)Kaufmann,Das Dritte Reich,p.368.
(212)Gerard P. Kuiper,‘German Astronomy During the War’,Popular Astronomy 54:6(June 1946),p.278;Ley,‘Pseudoscience in Naziland’,p.93.
(213)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22-3;Anna Bramwell,Blood and Soil:Richard Walther Darré and Hitler’s ‘Green Party’,Abbotsbrook:Kensal,1985,pp.172-4;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64-73.
(214)Treitel,Science,pp.75,154-5. See also Ulrich Linse,‘Das “natürliche” Leben. Die Lebensreform’,in Richard van Dülmen,Die Erfindung des Menschen. Schöpfungsträume und Körperbilder 1500-2000,Vienna:Böhlau,1998;Uwe Heyll,Wasser,Fasten,Luft und Licht. Die Geschichte der Naturheilkunde in Deutschland,Frankfurt am Main:Campus,2006;Wolfgang R. Krabbe,Gesellschaftsveränderung durch Lebensreform. Strukturmerkmale einer sozialreformerischen Bewegung im Deutschland der Industrialisierungsperiode,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4.
(215)Bramwell,Blood and Soil,pp.174-7.
(216)Piers Stephens,‘Blood,not Soil:Anna Bramwell and the Myth of “Hitler’s Green Party”’,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14(2001),p.175.
(217)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19-23.
(218)Treitel,Science,pp.153-4.
(219)Treitel,Science,pp.154-5;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31-8.
(220)Treitel,Science,pp.153-4.
(221)Harrington,Reenchanted Science,pp.23-33;Ley,‘Pseudoscience in Naziland’,pp.93-4;Kuiper,‘German Astronomy During the War’,pp.263-80.
(222)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22-3;Mees,‘Hitler and Germanentum’,pp.255-70.
(223)Treitel,Science,p.107.
(224)Staudenmaier,Between Occultism and Nazism,pp.146-7,153-4,159.
(225)同上,pp.161-2。
(226)同上,pp.163-5。
(227)Eva Johach,‘Entzauberte Natur? Die Ökonomien des Wunder(n)sim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Zeitalter’,in Geppert and Kössler,eds,Wunder,pp.189-95;Harrington,Reenchanted Science,p. xx.
(228)Mogge,‘Wir lieben Balder’,pp.46-8;Puschner,‘The Notions Völkisch and Nordic’,pp.29-30;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45-63,178-9.
(229)诺恩为北欧神话中的命运女神。——译者
(230)Artamanen,亨切尔根据中古德语词根造的单词,意为“农业人”。它主要是一个青年运动,结合了当时流行的生命改良运动,成员大多反对现代城市生活,崇尚模仿和恢复乡村生活习俗,以振兴雅利安民族。——译者
(231)Puschner,Die völkische Bewegung,pp.189-201.
(232)Heike Jestram,Mythen,Monster und Maschinen,Cologne:Teiresias Verlag,2000.
(233)同上,pp.55-62,89-92。
(234)除了弗里奇和李斯特之类激进的种族-秘术论者及优生学家,整体论的支持者里也有恩斯特·亨克尔、阿尔弗雷德·普吕茨、汉斯·德里施之类名声不错的威廉二世时期的科学家。Harrington,Reenchanted Science,p. xx。
(235)Willy Ley,Watchers of the Skies:An Informal History of Astronomy from Babylon to the Space Age,New York:Viking Press,1966,p.515;Christina Wessely,‘Welteis,die “Astronomie des Unsichtbaren” um 1900’,in Rupnow et al.,Konzeptionen,pp.163-4;Martin Halter,‘Zivilisation ist Eis. Hanns Horbigers Welteislehre-eine Metapher des Kaltetods im 20. Jahrhundert’,Sudwestrundfunk SWR2 Essay(Redaktion Stephan Krass). Dienstag,15.7.2008,21.33 Uhr,SWR2。霍尔比格和布拉瓦茨基一样,他在创建自己的理论时,更多是受到了科幻小说而非科学的影响,在这个例子中,指的就是上文提及的由慕尼黑作家马克斯·豪斯霍费尔的作品《星球之火》(Planet Fire)。在豪斯霍费尔的小说中,未来的慕尼黑社会,自由主义风气极浓,腐败堕落,无可救药,但在堕落的周期中,受到启发,惊醒过来,在下了一场猛烈的冰流星雨之后终得重生。
(236)Ley,‘Pseudoscience in Naziland’,pp.95-6;Robert Bowen,Universal Ice:Science and Ideology in the Nazi State,London:Belhaven,1993,pp.5-6.
(237)Halter,Zivilisation.
(238)Christina Wessely,‘Welteis,die “AstronomiedesUnsichtbaren” um1900’,p.171;Ley,‘Pseudoscience in Naziland’,pp.96-7.
(239)Halter,Zivilisation,p.83.
(240)Wessely,‘Welteis,die “Astronomie des Unsichtbaren” um 1900’,pp.186-7;Ley,‘Pseudoscience in Naziland’,pp.95-6.
(241)http://www.mpiwg-berlin.mpg.de/en/research/projects/deptIII-ChristinaWessely-Welteislehre;Fisher,Fantasy,pp.3-4.
(242)正如Christina Wessely所说,“冰世界理论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它以将科学术语和方法论同广为流行的形象和老生常谈混合在一起,造成了颠覆性,而产生吸引力”。http://www.mpiwg-berlin.mpg.de/en/research/projects/deptIII-ChristinaWessely-Welteislehre。
(243)Wessely,‘Welteis,die “Astronomie des Unsichtbaren” um 1900’,pp.182-6.
(244)同上,pp.174-8。
(245)http://www.mpiwg-berlin.mpg.de/en/research/projects/deptIII-ChristinaWessely-Welteislehre.
(246)Wessely,‘Welteis,die “Astronomie des Unsichtbaren” um 1900’,p.166;Halter,Zivilisation.
(247)http://www.mpiwg-berlin.mpg.de/en/research/projects/deptIII-ChristinaWessely-Welteislehre.
(248)Treitel,Science,p.190.
(249)同上,pp.25-6。
(250)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p.177-93;Mosse,Masses and Man,pp.210-12.
(251)Wessely,Cosmic Ice Theory.
(252)Williamson,Longing,pp.294-8.
(253)Rupnow et al.,eds,Pseudowissenschaft.
(254)Geppert and Kössler,eds,Wunder,p.26;Saler,‘Modernity and Enchantment’.
(255)Treitel,Science,p.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