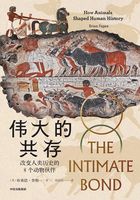
序言
从乔治·布封(1707—1788)写作《自然史》开始,历史就不再只是人类的历史。《伟大的共存:改变人类历史的8个动物伙伴》正是继承了这种自然史的精神,将人类最为熟悉的8种动物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加以审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别样的历史阅读体验。
地球有46亿年历史,人类是地球上很晚才出现的动物。农业的出现不过10 000多年,而广义上的“文明人”在这个地球上已生活了200万年。换言之,人类99%的时间是在狩猎和采集的阶段中度过的。长期以来,人类与动物基本是平等的,人只是动物中的一分子。在大多数时候,其他动物是人的猎物;但在有些时候,人也可能是其他动物的猎物。
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彻底改变了人与动物的关系。用一位法国学者的话说,农业使人依附于土地并“脱离”自然,使人与众不同,从而使人上升到一个比动物更高的层次。
农业生产出大量粮食,当农业出现剩余时,驯化就出现了。驯化动物消耗了定居社会借以生活和生存的谷物剩余。这种“拘兽以为畜”的驯化过程,从10 000多年前人类驯化狗开始,然后是肉用动物鸡、羊和猪,接着是动力型动物牛和驴,最后出场的是马和骆驼。
亚里士多德曾说,动物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礼物,“既是好劳力,又是美味佳肴”。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驴、牛、马、骆驼之类的动力型动物,它们让人类获得了更大的肌肉力,使人类不仅可以耕种更多的田地,而且可以运输更多货物,或更快速地移动,人类世界由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要超过后来出现的火车、汽车和飞机。
《伟大的共存:改变人类历史的8个动物伙伴》讲述的就是人类与动物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作者布莱恩·费根作为剑桥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士,具有一般人所不及的专业视角和广博知识。在费根看来,人类不仅改变了动物,动物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用书中的话来说:“人类与动物地位平等,本无高低之分,直到人们开始驯化各种动物,支配和从属关系才出现。”
荀子曰:“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对抗。中原社会重视牛和猪,草原社会则重视马和羊,实际上,这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的对抗也是两种动物之间的对抗——牛相对于马拥有生产优势,而马相对于牛则有着军事优势。
本书虽然也涉及猫和鸡等动物,但主要聚焦于狗、山羊、绵羊、猪、牛、驴、马和骆驼这8种动物,从它们被驯化的经过,到融入人类社会后产生的重要影响,书中都有独特的发现与揭示。
人们或许想不到,狗是人类驯化的第一种动物。很明显,狗的驯化是人类狩猎采集时代的产物。当时,面对冰期结束、全球急剧变暖所带来的挑战,人与狼在狩猎过程中结为命运共同体,狼慢慢变成了狗。由此算来,狗和人在一起的时间已有大约15 000年之久。
在农业社会,山羊、绵羊、猪为人类提供了稳定的肉食来源,这样的社会比狩猎社会更加安全、更加可预期,这3种貌不惊人的动物也成为人类的财富源泉。在汉字中,屋里养猪为“家”,由此可见猪对农业定居者的重要性。而山羊和绵羊也支撑了游牧社会的生存,牧民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依靠羊奶和羊毛生活,并不轻易地宰杀羊,因此羊群也是财富的象征。
牛的驯化非常早,这种大型动物对人类来说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牛不仅被用来拉车,也被用来耕地,奶牛则提供了高营养的牛奶,牛肉也是一种极其完美的肉食。
对牛的驯化体现了人类伟大的创新能力。用书中的话说,“驯化是一个共生的过程,是动物和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牛一旦被人类驯化,很快就成为人们可以积累的财富,以及向外炫耀的家产和竞相争夺的对象。在许多非洲社会,牛实际上相当于“钱”。
在非洲古老的努尔人部落,人们把牛视若神灵,牛群在这里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努尔人对牛的关怀无微不至,为牛生火驱蚊,为牛而不停搬迁,为牛制作装饰品,以保护它们免遭骚扰和攻击,他们甚至用牛的形态和颜色为自己取名字。这让一些外来人感叹:“努尔人可谓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尽管努尔人很喜欢吃肉,但他们绝对不会为了吃肉而杀牛。他们只有在牛死掉以后才会吃其尸体,以此表示对牛的热爱。
书中这段叙述,堪称人与动物“伟大的共存”的难忘一页。虽然努尔人是人类初民,不能跟现代人相提并论,但实际上,牛在现代印度依然享有尊贵的地位,去过印度的人都对那些在大街上闲庭信步的牛群印象深刻。
如果说人类通过驯化植物发明了农业,那么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则是牛,甚至连牛粪也极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费根将牛称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引擎的同时,将驴和骆驼称为皮卡车。在传统时代,陆路运输极其困难,每头驴大约可以载重75千克,每天行进大约25千米,由数十头驴组成的毛驴商队相当于陆地上的海洋船队。骆驼负重更大,速度也比驴更快,哪怕不喝水,也能在酷热的环境下行走很远的距离。如果说驴大规模地开启了商队贸易的全球化进程,那么骆驼则进一步将这一进程推而广之,将非洲和亚洲的财富带到了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换言之,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牲畜帮助我们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世界。
事实上,正是由于动力型动物的出现,人类社会才有了剩余,而剩余产生了掠夺和贸易。无论是在丝绸之路还是在茶马古道,都是这些驯化的动力型动物帮助人完成了古代贸易。同时,这些动物也引发了残酷的战争。
越靠后出场,往往越重要。费根在本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写马。在他看来,马将动力型动物对人类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在古罗马时代,良马稀有而昂贵,其价值相当于7头公牛、10头驴或30名奴隶。这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与动物生命相比的价值。
对人类历史来说,驯化马具有颠覆性意义,游牧民族因此获得了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将生产技术变成军事技术,从而获得不可思议的战争能力。从最早使用马拉战车的赫梯人与埃及人,到后来的匈奴人与蒙古人,战马成为他们征服世界的决定性力量。
本书着眼于整个人类世界,费根特别写到中国历代王朝用丝绸和茶叶换马的传统,并指出中原骑兵不敌游牧骑兵的深层原因并不在于马本身,而是人与马之间关系的疏离:“只有当人们在马背上生活和呼吸,并和马建立极为密切的关系后,战马才能成为一种强大有效的武器……无论是面对蒙古人时,还是在后来的几百年里,许多汉族骑兵似乎从未与他们的战马建立亲密的关系。很明显,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养马和骑马的门道,或者说没有真正掌握与马并肩作战的艺术,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人与动物之间密切关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产生过更加深远的意义。”
从本质上来说,人类与动物的密切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一旦历史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动物就遇到了一种全新的替代品——机器。
如果说这些驯化动物只是人类与自然合作的创造物,那么机器则完全由人类独立完成。从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机器步步为营,以不可逆的强势姿态进入人类世界,而动物则不断溃败和被淘汰。
机器不仅改变了人与动物,也改变了人看待动物的态度。在笛卡儿眼中,动物也不过是一种机器。而“最好的动物是那些吃得最少、干得最多的牲畜”,正如最好的机器消耗最少、干活最多。这就是被现代人奉为真理的效率。
1699年,法国科学院对马和人的工作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1匹马所做的功相当于6人至7人所做的。1775年,瓦特蒸汽机开始商业化生产,马力被定义为蒸汽机的功率,1匹马在1秒内把75千克的水提高1米为1马力。这似乎也是动物与机器此消彼长、完成交接的历史瞬间。
很多人不知道,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蒸汽机驱动机器,而驱动蒸汽机的是煤,这些煤仍旧来自动物。在英国黑暗的煤矿中,有多达70 000匹矿井马在没日没夜地工作。因为矿井狭小,人们一般都用马驹。这些骟马或公马,从出生就在黑暗的矿井中,它们性情温顺,身体强壮,吃苦耐劳,可连续服役20年。这些马长期在矿井中工作,甚至从未见过阳光,近乎全盲,它们即使退役后也无法适应牧群和露天生活,所以都活不长。
与矿井马相比,曾经驰骋疆场、扫平天下的战马命运更加悲惨,在钢铁和枪炮面前,它们常常还没有来得及昂首扬蹄,就已经灰飞烟灭。
机器取代了马后,火车和汽车便出现了,现代社会就这样来临了。一切都发生了巨变,动力型动物被机器取代了,肉用动物则直接变成了机器——将饲料转化成肉、蛋、奶的食物生产机器。
一位经济学家说,老鹰和人类都吃鸡肉,只不过老鹰越多,鸡越少;而人越多,鸡也越多。今天的地球上,人类只有70亿,而鸡则有200多亿。但在人类眼里,鸡只是用鸡蛋制造鸡蛋或鸡肉的工具。
现代集约化养殖场追求的是“快周转、高密度、高机械化、低劳动力需求和高产品转化率”,这使得人类对待猪、鸡、牛等动物的方式都面临严重的伦理拷问。1964年,英国动物福利活动家露丝·哈里森出版了《动物机器》,该书与《寂静的春天》一起引起了社会震动。费根在本书中基本继承了哈里森的观点,一方面对动物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对人类的“选择性仁慈”予以批评。他想提醒人们,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也多少暗示着人对待人的态度。
一部人类史,也是一部人与动物的互动史,再回首,人与动物的关系免不了始乱终弃。在机器时代,人与动物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人与机器的关系越来越近。或许,猫和狗是唯一的例外;又或许,人类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机器狗和机器猫真的能代替狗和猫吗?人生短暂,而机器永远不死。
1808年,诗人拜伦最喜爱的“水手长”死了,拜伦为这只纽芬兰犬写下墓志铭:“有人的所有美德,而没有人的恶习。”
杜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