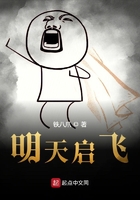
第23章 干活喽
第四天,干活喽!
吃饱喝足,再穿的暖暖的,干活,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村民热情高涨,开始把村头荒山上的杂草石头清理干净。
虽然不理解,这座不大的小山,虽然是土质的,但种不了庄稼啊。
但不妨碍努力干活。
能吃饱,叫干啥干啥,别说开荒,就算去杀人,也无妨。
别不信,那些大头兵们,也没听说几个能吃饱的。
杨大脸试图抱起一块大石头,憋得脸上通红,也没能抱起来,只能拿起镰刀割干草。
身边过来一个人,两手一伸,轻松抱起那块石头,轻松丢进一个大坑中。
杨大脸一脸的羡慕,这天生的,比不了啊,不由得说道:“牛哥,你厉害!今天能领两斤面了。”
大锅饭,不存在的,好好养了下身体,补充了下亏空,这时候是随便吃的。
但一开始干活,区别就出来了。
干什么活领多少粮食,那是有数的,割草的,每天只有一斤面,吃饱有点难,但肯定饿不着,搬石头的就有两斤,吃饱肯定没问题了,说不定还有剩。
那牛哥却一脸的郁闷:“唉,干得多吃的多,还有个不能干活的婆娘呢。”
不干活的,老人孩子特殊照顾,有的吃。成年人,孕妇有的吃,还是最好的。其他人除非特殊批准,必须干活,包括裹脚的女人。
杨大脸笑道:“让你当年作死,觉得自个有点钱粮了,就讨了个小脚婆娘,活该!”
那人也不生气,人生难得一知己,穷苦人家,也是有知己的。
他叫杨典,因有把子力气,被叫做大牛。
和杨大脸同日出生,家又离得近,从小一起玩到大。长大了呢,又同年结婚,过了些年,这里是皇庄了,两人的孩子又近乎同时死掉。
一些玩笑话而已,杨大牛笑笑,就开始继续搬石头。
一天的劳作结束之后,两人结伴回村,拿着一张纸在村头领粮食。
杨大脸想了想,要了一斤白面,似乎有点奢侈,但皇帝可是许下了能吃饱的,吃就完了。顺便还领了一小块咸菜,这个是送的,每人都有。
杨大牛也想了想,要了三斤高粱面。一斤白面换一斤半高粱面。话说这高粱面可不好吃,又苦又涩,但没奈何,想赚这份粮食,就得下死力气,不吃饱可不行。
两人结伴回到家,对,两人都是积极分子,一起住在原来管事太监的石头房里面。
一个小脚女人,晃晃悠悠的接过杨大牛手里的高粱面,准备做饭。锅已经发下来了,有家庭的都是自己开火。
杨大脸笑了笑:“嫂子,一起做吧,俺媳妇累了一天了,让她歇会好了。”
大牛的媳妇拿眼看了下大牛,看到他点头才接过杨大脸手中的白面,去做饭了。
杨大牛垂头,从院子里的井里打上水来,倒了两碗,递给杨大脸一碗,一时间,什么话也没说。
尽在不言中,搭伙做饭,可是占了老大便宜的,别看人家拿的少,人家也吃的少啊,最终,还是自个拿高粱面换的别人白面吃。
俩男人沉默着喝水,没多久,杨大脸的媳妇也回来了,风风火火的拿着一包粮食,还有一小包柳芽,交代了几句,就忙活着做饭去了。
男人,去开荒,女人,去摘柳芽。粮食是绝对不够吃的,任何能吃的,都不能放过。
皇帝可比底下人狠多了,老百姓摘柳芽,只摘够得着的,太高的,废老大力气爬树去摘柳芽,吃到嘴里的还没消耗的多呢,不值得。
但皇帝下令,能吃的,一根芽都不许剩,全部清空。
但是,爬树可不是小脚女人能干的事,皇帝又把喜欢爬树的娃娃全部拉走了,男人去开荒,只能女人去。
杨大牛羡慕的看着杨大脸的媳妇,女人,什么时候也能和男人一样赚粮食了。
沉默了一会,忽然开口:“这裹脚,害人不浅啊!”
杨大脸懒得回话,当年你娶这个婆娘的时候,可是好生跟咱炫耀了好久呢。
倒是声音大了些,让在厨房做饭的女人听到了,满脸幽怨:怪我喽!
高粱面混着白面,夹杂着柳芽的馒头,让所有人都吃的很满意,能吃饱,有啥好抱怨的呢。
只有一个小脚婆娘,心中烦闷,别的女人,都干活了,咱干不了啊,又不是娃娃,就算放开裹脚布,也是那样了。
但第二天,她的苦恼就结束了,有太监来传令,寻找会做衣服的女人,每人每天八两标准粮。
没话说,赶紧上前,表示咱从小女红做的好,保证不会耽误皇帝的事儿。
再不做事,都给别人笑死了啊。
那太监表示,要考核,先给咱家缝下衣服让咱看看。
女人没话说,好有道理,接过太监的棉袄细细的缝了起来。
随后跟随太监来到一个刚刚建好的房屋里面,巨大原木支撑的房屋极大,极为宽敞,里面已经无数的人在等着。
“呀,吃亏了啊!”
都是一个村里的,大部分相互都认识,这一打听,好吗,皇帝就要去太监带人,压根没提考核的事情。
考核?还用考核吗,这年头,不会女红的女人才是百里挑一的,嫁人都难的那种。
再说,就算不会也无妨,这里,是个现代化管理模式的手工作坊。
女红再好也没用,每个人都没有完整处理一件衣服的可能,全部细细的分成无数的步骤,每人负责一块。
杨大牛的媳妇,虽然小脚,但针线活极好,分了个很好的工作,最后缝制衣服。
这可比其他活计强多了好吧。
之前收集起来的破烂衣服,已经洗的干干净净。
有人专门负责把碎布剪整齐,拿着一个大剪刀一天不停的剪,那手都磨出血泡来。
还有人专门把剪掉的碎末收集起来,捣碎,再用细网布包起来,作为棉袄或者棉被的芯,一天下来,浑身都是毛毛,能不痒吗。
而杨大牛的媳妇,负责把处理好的棉芯,和崭新的棉布缝在一起,坐着就行,除了手上出点力气,又干净又轻松,算是最好的活计了。
就这活,每天能领八两粮食,实在太幸福了。
但女人心里还有些隐忧,这么好的工作,又能做几天呢,村里的破衣服,又能有多少呢?
纯粹是杞人忧天。
这边活还没做完,一大车一大车的破衣服,连绵不断的送来。
在这杨家村呆了几天之后,朱由校暂时离开了,去了附近另外一个皇庄,所有京城附近的皇庄,全部清理一遍。
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是不能指挥别人做的,只能手把手的教,带头做。
暂时先教太监,这是挺好的选择。
太监吗,没了子孙根,欲望着实很低,而且作为皇权的附属物,离开皇权,他们什么也不是,相当听话。
而且大部分太监是识字的,当年也不知道哪个皇帝,一时兴起,在皇宫中办了扫盲班,一直延续至今。
虽然说,扫盲的效果比起从小学习的,差了很多,但朱由校宁愿用扫盲过的太监,也不用读书人。
皇帝出京,百官默许,这群见鬼的臣子!
但官员可不是一条心的,整体上,臣子是和皇权对抗的,但具体到个人,也不缺乏愿意投奔皇帝的。
但朱由校提出了一个相当蛋疼的要求,想跟着我混,行啊,我家佃户,土地是我的,人现在也归我了,所有财产也归我了,对吧。
你想来也行,把所有家产,所有的,全部交出来。
无数人狼狈告退,不可能的事情!
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现在朱由校正接见一个传统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