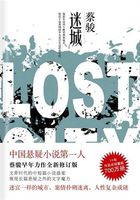
第1章 迷城(1)
(引子)
已经是后半夜了,叶萧缓缓地走在那条似乎无穷无尽的官道上,大路上覆盖着一层白雪,身后留下两行清晰的足迹。当他以为自己永远都无法到达终点时,忽然,那座城市出现在了视野尽头。
他站在山冈上眺望那座城市,只见一片白茫茫的雪原在冷月下泛着银光,他惊诧于这南国的冬天竟会有这样的雪野。越过那道在雪原中蜿蜒起伏的官道,便是南明城了。
隔着黑夜中的雪地远远望去,那座城市就象坐落于白色海洋中的岛屿。这个雪野中的怪物有着无数黑色的棱角,突兀在那片雪白的平地中,叶萧的眼睛忽然有些恍惚,不知是因为这大雪,还是远方那虚幻的庞然大物。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岗上看了很久,一切又显得有些不真实了。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令他印象深刻的第一眼之后,他永远都难以再看清这座南方雪野中的城市了。
叶萧知道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他摸了摸背后藏着的剑鞘,快步走下了的山岗。
二更天了,丁六听到城墙下更夫的梆子声在南明城的死寂中敲响,他清醒了一些,抬起头看着那轮清冷的月光,那被厚厚的眼袋烘托着的细长眼睛忽然有了些精神。他挪动着臃肿的身体,继续在月满楼前的小街上走着。
丁六的步子越来越沉,雪地里留下深深的脚印。他嘟嘟囔囔地咒骂着这寒冷的天气,浑浊的气体从口中喷出,又被寒风卷得无影无踪。酒精使他脸色通红,他后悔没喊轿夫随行,但每次坐上轿子,轿夫们就会暗暗诅咒他,因为他的体重使所有的轿夫都力不从心。他又想起了刚才月满楼里,那些女人们身上留下的胭脂香味,这味道总在他的鼻子附近徘徊,就连风雪也无法驱走。
拐过一个街角就要到家了,习惯于深夜回家的他会举起蒲扇般的手掌,拍打着房门,年迈的老仆人会给他开门,乡下来的十五岁裨女会给他脱衣服,端洗脚水。最后,他会走进屋里给躺在被窝里瘦弱的夫人一个耳光,斥责她为什么不出来迎接。
再走二十步就到家门口了。
忽然,他停了下来。
他停下来不是因为他改变了主意,而是因为他忽然听到了什么声音,这声音使他的心脏在厚厚的胸腔猛然一跳。丁六忽然有些犹豫要不要回过头看一看,不,也许只不过是寒冬里被冻坏了的老鼠在打洞,或者是——终于,他把自己那颗硕大肥重的头颅回了过来。
太阳升起在雪地里,南明城的每一栋房子都覆盖着白雪,房檐下一些水珠正缓缓滴下。
南明城捕快房总捕头铁案抬着头,天上的太阳与周围的一切融合在了一起,光芒如剑一般直刺他的眼睛。铁案缓缓地吁出一口气,看着从自己口中喷出的热气升起又消逝,忽然觉得有些无奈。他又低下了头,看着地上的尸体。
雪地上的死者仰面朝天,肥大的身躯就象一张大烧饼摊在地上,显得有些滑稽。铁案轻蔑地说,死得真象头猪。
铁案认识这个死者,甚至对他了如指掌。死者叫丁六,经营猪肉买卖十余载,在全城开有七家肉铺,生意兴隆,家境殷实。说实话铁案很厌恶他,当年丁六是靠贩卖灌水猪肉发家的,至今仍在从事这种勾当,只因贿赂了地方官,才能逍遥法外,要不然铁案早就用链条把他锁起来了。
虽然铁案对丁六充满厌恶,但他还是伏下身子,仔细查看丁六咽喉上的伤口。是剑伤,伤口长两寸一分,深一寸二分,完全切断了气管,但没有丝毫触及动脉。显然凶手是故意这么做的,丁六仅仅是被割断了气管,不可能一下子就死,他是在无法呼吸的痛苦中渐渐死去的。
忽然,铁案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黑夜的雪地中,寂静无人,只有丁六臃肿的身体倒在地上,他的咽喉有一道口子,气管被割断,其中一小截裸露在风雪中。丁六也许还茫然不知,他倒在地上猛地吸着气,然而从口鼻吸进的空气,却又从喉咙口那被割断的气管漏了出去。他不明白此刻的呼吸只是一种徒劳,他那肥胖的身体迅速地与空气隔绝开来,然后他开始不停地抽搐。一开始丁六的脑子还是清醒的,他应该记住了杀死他的那个人的脸。最后由于断气,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在绝望中丧失所有的意识。铁案考虑到死者的体形,他推测这一痛苦过程大约持续了半柱香的时间。
铁案又回到现实,许多人在雪地里围观,公差和衙役在维持秩序。丁六的老婆来了,这精瘦的女人尽管脸上残留着许多丁六赐给她的掌印,可依然不要命似地往丁六那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身体上扑去。一个公差拉住了她,铁案的耳边响起了女人的尖声嚎叫,这刺耳的声音让铁案心烦意乱。他知道仵作马上就要来拉尸体了接下来做的就是破案,缉拿凶犯,捉拿归案,官府审判,最后等待凶犯的将是秋后处决,这一切,对于办了二十多年案的铁案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了。
他低着头拐过一个小街口,见到了那个叫阿青的小乞丐。他停下来怔怔地看着小乞丐,在阳光照不到的街角,阿青静静地坐在一堆废棉絮里,身上裹着一件破得象筛子似的棉袄。铁案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停下来,小乞丐特别脏,看不出多少年纪,脏脏的小脸盘上有着一双特别明亮的眼睛,与被抹黑了的脸形成鲜明对比。铁案忽然想起了什么,但瞬间又忘记了,也许自己真的老了,他长叹一声便离开了。
阿青蜷缩在大棉袄里,静静地看着那高大的官差离去,然后拍拍身下的破棉絮说,快出来吧,官差走远了。
叶萧终于把自己的头从那堆棉絮中探了出来,面无表情地看着阿青的脸。
寒夜里,一堆篝火悄悄地燃烧着,不断跳动的火光映红了这间破庙里一切,也映红了阿青脏脏的脸,她的脸终于有了些血色。她转过头看着身边的叶萧,轻轻地问——你从哪里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叶萧淡淡地回答。
不知道?你真奇怪,那你为什么来南明?
我来找一个人。
谁?
王七。
王七?阿青觉得这个名字好象有些熟悉,但又实在记不起来,也许是因为这个名字太普通了,随便哪条小巷里都能找出一个王七来。她又问叶萧,你找的那个王七是什么人?
他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那你找王七干什么?
与他比剑,而且,我要打败他。
可你甚至还不知道他是谁?阿青有些莫名其妙。
你觉得这重要吗?篝火照耀下的叶萧的脸忽然冷峻了起来。
阿青看着他的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眼前的少年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她是在昨夜三更天时看到叶萧的,那时她正睡在这间破庙里,从外面传来的声音使她惊醒,她跑出来看到了这少年,他穿着破旧的衣服,独自行走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阿青看他冻得发抖,就把他带回破庙,让他睡在神像前的供案上。
阿青忽然问,今天早上,那个公差走过的时候,你为什么立刻就躲到棉絮堆里去了呢?
因为昨夜我是翻越城墙进来的,我不想被官府抓住。
怪不得,你的本事真大,能翻城墙?
叶萧不回答,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狭小的破庙里又限于了沉寂,篝火继续燃烧着,寒风从破庙的缝隙里刮进来,吹坏了角落里的许多蛛网。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叶萧终于说话了——阿青,你说话怎么象个女孩子?
你说什么?
我说,你说话的声音象个女孩子。
叶萧以为她是个男孩子。其实,几乎所有认识阿青的人都这么认为,她总是披散着一头发出臭味的头发,裹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袄,每天都是脏兮兮的样子,没人会把她与小姑娘联系在一起。阿青也愿意别人把她当成男孩,一个住在破庙里的以乞讨为生的穷小子。
嘻嘻。
阿青象所有的男孩那样对叶萧傻笑了一下,然后就倒在乱草堆里睡觉了。
叶萧依旧坐在篝火前,独自面对着越来越微弱的火苗。
朱由林看到自己走在一片密林中,密林不见天日,只有乌鸦的叫声响起,在树木与枝叶间回旋着。他握着佩剑继续向前走着,乌鸦纷纷向他飞来,他的帽子被叼走了,锦袍被啄破了,甚至玉带也被抢去了。最后,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没有了,只剩下手上一把剑。
这时密林中出现了一个人影,那个人的脸逆着光,一言不发地走近了朱由林,当朱由林即将看清他的脸时,那人忽然扬了扬手,一道寒光从他手中出现。朱由林刚要拔剑,就感到自己的喉咙口有一阵彻骨的凉意,一阵风正从咽喉灌进他的身体,他有一股脖子被别人掐住的感觉,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当今大明天子的侄子世袭南明郡王朱由林终于醒了过来。他喘着粗气,坐在紫檀木的大床上,透过纱帐向外看去,寝宫里一片黑暗寂静,只在宫室的一角,刻漏还在继续滴着水。听到这每夜陪伴他的刻漏声,朱由林终于相信刚才只不过做了一个梦。他担心天寒地冻,万一刻漏壶里的水结冰了的话,他就真的要陷入无边的恐惧中了。
朱由林离开了他的大床,披了件皮袍走到寝宫另一边,忽然闻到了一阵奇特的熏香,耳边似乎又响起了惠妃的笑声。他又想起了刚才那个梦,自从这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降临南明城起,他每晚都会做到这个梦。
朱由林走到了寝宫的窗前,缓缓推开了窗,黑夜里什么都看不清,只有天上的冷月放射着清辉。
又下雪了。
南国细小的雪籽,轻轻地落在南明的街巷中。叶萧有些累了,他靠在一间店铺边,静静地看着前方的十字路口。身体靠在墙上,背囊里的剑硬梆梆地,几乎嵌入了后背。剑柄藏得非常隐蔽,即便从他身后经过都很难察觉得到,但如果需要,他能以最快的速度将剑从背后拔出,指向敌人的咽喉。
一些雪籽落在他脸上又渐渐融化。忽然,店铺的门开了,老板杨大走出店门,迎面看到了这个靠在墙边的少年。
杨大端详了叶萧一会儿,看出他不是本地人,杨大笑了笑说,小兄弟,下雪天的,进来坐坐。
叶萧跟着杨大走进了店铺。店铺宽敞豪华,架子上摆放着各种药材,叶萧立刻闻到了一股久违了的山野味道。
小兄弟,把你背后的东西拿出来吧。
叶萧一惊,他的手立刻探向背后,悄悄地抓住了剑柄,当他准备先发制人时,却听到杨大说,小兄弟,我看到你后面的草药了,是不是三仙草?
原来是背囊里的三仙草露了出来,几天前叶萧路过一座大山时,曾采了几把这种名贵的草药。他放开了握着剑柄的手,将背囊里草药拿了出来。
小兄弟,我就知道你是来卖草药的,把这些三仙草卖给我如何?
叶萧心想自己留着也没用,随口一说,好的,三十文钱怎么样?
杨大没想到这少年开价居然如此低,显然不识货,在杨大的店铺里,这样的三仙草至少能卖五十两银子。杨大觉得今天很走运,却板着脸说,小兄弟,你开的三十文的价钱高了些,不过,算我们交个朋友,就三十文,我要了。
杨大仔细数了数三十个铜板,串好了交给叶萧,叶萧没有点就塞进了怀里。
杨大问他,小兄弟,你不是本地人吧?
叶萧点了点头。
小兄弟来南明干什么呢?
我来找王七。
王七?这个名字很耳熟。杨大想了想,又问,你找他干什么?
和他比剑。
不,你不可能和他比剑的。
为什么?
因为王七已经死了。
清晨时分,雪终于停了。
铁案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走进天香药铺,他掀开帘子,在柜台后面看到了杨大的尸体。
杨大坐在椅子上,上半身倒在桌子上,脸朝右,左耳贴着桌面,右侧有一个算盘,右手甚至还搭在一枚算珠上,头的前方摊着帐本,毛笔落在桌子上。铁案仔细地看了看毛笔尖上的墨汁,已经完全干了。凶案应该发生于子时,铁案知道杨大一直都有半夜里算帐的习惯,因为杨大的贪财是出了名的。他看着杨大的脸,那张脸什么表情都没有,眼睛还睁着,大而无光的眼睛就象翻白肚皮的鱼。杨大的伤口在咽喉,一道细细的口子,长两寸一分,深一寸二分,与两天前丁六身上的伤口一模一样。还是准确地切断了气管,刚好没有触及动脉,所以血流得很少。铁案明白两起凶案必然出自于同一人之手,而且凶手故意要使死者在临死前忍受无法呼吸的痛苦。想着想着,铁案心里忽然一沉。
铁案拉开了杨大身边的抽屉,里面放着银票和银元宝。他又看了看桌上的帐本,帐本里的金额与抽屉里的实际钱款相符,一文不少,显然凶手不是为劫财。不过,看完帐本后,铁案对杨大更加鄙夷了,因为从帐本上可以看出,杨大几乎每做一笔生意,都在短斤少两地欺诈他人的银子,甚至还能从帐本上看出他贩卖假药。
最后,铁案从杨大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把草药,他把这些草药放到眼前仔细地看了看,忽然想起几年前南明王府里一位王妃急病,正是铁案跑到杨大的店铺里买来了这种名贵的草药才救活了王妃的性命,铁案至今还记得这种草药的名字——三仙草。
破庙里,篝火依旧点着。
你找到王七了吗?
小乞丐阿青轻声问着叶萧。
叶萧摇摇头,他们说王七已经死了。
也许他们说的王七,并不是你要找的那个王七。
我不知道。
叶萧茫然的说,他转过头看着阿青,跳跃的火光使他的脸忽明忽暗。
那你还会找下去吗?
是的。
如果王七真的已经死了呢?
不,王七不会死的,永远都不会。
叶萧冷冷地说。
忽然,一阵冷风把庙门吹开了,篝火被吹灭了。狭小的破庙陷入了黑暗中,阿青早就习惯这种环境了,但她还是有些害怕。
你在发抖?叶萧问她。
我在这破庙里住了十几年了,从来不会发抖。
不,你在发抖。
叶萧忽然伸出手抓住了阿青的肩膀,阿青真的发抖了。黑暗中她听到了叶萧的声音——现在没有火了,你一定很冷,来,靠在我身上,我们两个互相以身体取暖。
阿青有些犹豫,她明白,叶萧并不知道她其实是女儿身,在叶萧眼里,阿青不过是个要饭的穷小子。阿青最后还是顺势靠在了叶萧身上,叶萧的双手抓住她的肩膀。她非常瘦,叶萧轻声地说,你的肩膀怎么那么单薄,薄得就象一只小猫的骨头,我怕我轻轻一捻,就会把你捻碎。
那你把我捻碎啊。阿青吃吃地笑了笑说。
叶萧终于也笑了一声。他把阿青揽得更紧了,他的两只手象铁箍一样紧紧地箍住了阿青,两个人的身体贴在一起,体温互相传递着。
阿青,你多大了?我看不出你的年纪。
大概是十六吧,也可能十七、十八,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可你看上去好象没这么大。
那你呢?
我十九岁了,我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里,我只知道我要找一个人,这个人在南明城,他的名字叫王七,我要与他比剑,打败他。
你找不到他就不离开南明?
是的,阿青,现在你还冷吗?
不冷了。
那你为什么还发抖?叶萧在阿青的耳边说,他口中吹出的粗重的气息掠过阿青小小的耳垂。
阿青没有回答,她发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自己正躺在一个男人的怀中。她把双手挡在自己胸前,其实她的胸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两朵刚刚绽开的小小嫩芽。
还有,就是一块胸前的玉佩,这是她身上唯一看起来不像小乞丐的东西。
叶萧也在她胸口摸到了这块玉佩,这是从哪里来的?
我也不知道,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玉佩看起来很是精美,那么多年来没有被其他乞丐抢走,已经算是阿青天大的走运了。